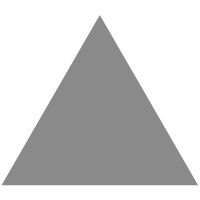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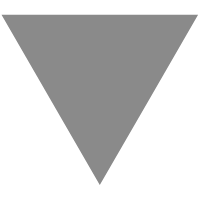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五台碎片(下):路过唐诗现场
source link: https://mp.weixin.qq.com/s/vRATGtu2lu8ZEJ8Q0g25gQ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五台碎片(下):路过唐诗现场
千年一寺看佛光。传奇的佛光寺一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看系列”清单里,也已从书籍资料中看过许多对佛光寺东大殿的描述,但不知何故,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不知道它建在高台之上,处于山岩的环绕之中,甚至直接背靠岩壁。
这种疏忽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当我真的来到了佛光寺,从第一层院落往上看,只能看到树木掩映下一部分的殿体和屋顶,而你并不能确定那是否就是传奇之所在。就像古建筑中的影壁或“翠幛”,遮挡视线的同时也赋予观看者无尽的遐想。
可是谈何容易?火灾、虫蚀、战乱、地震、风霜雪雨、朝代更迭、灭佛运动……任何一个因素都是木构建筑的天敌。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但佛光寺东大殿的确就奇迹般地挺过了这一切(包括8次五级以上地震),历经千年,金刚不坏。更厉害的是它至今未曾落架维修过,完好地保存了唐大中十一年的原建原物。据说日本虽然也保存有建造年代甚至比佛光寺更早的木结构建筑,但一般每隔两三百年就要落架大修一次,每大修一次就要更换三分之一的构件,所以现在的日本木构古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体量相等的古建筑模型了。如此说来,佛光寺东大殿的确堪称第一国宝。
而这当中还有一个幸运的误会。梁思成以敦煌壁画为“藏宝图”,按图索骥找到稀世之珍。但其实他们发现的佛光寺已不是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五台山图》中的佛光寺已在唐武宗灭佛时化为灰烬,而东大殿是在“会昌法难”十年之后重建的。也就是说,此珍宝非彼珍宝,但它仍是唐代的珍宝。
我不禁觉得,这样的幸运和奇迹都是上天对梁思成他们的褒奖。梁林都是富贵子弟、学术精英,本可以安坐书斋潜心学问,却不辞辛苦地连年在野外考察,为自己选择的事业鞠躬尽瘁。当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满目疮痍,破败凋零,兵荒马乱,盗匪横行,他们可说是主动冒着生命危险在吃苦受累。每到一处,都要详细测绘、照相、画草图,甚至清洗梁柱。我读到梁思成考察东大殿的记录,说他们需要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檩条则已被千百成群的蝙蝠盘踞,照相时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无以言表。
“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梁思成写道,“因为那时我们生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正是这样的担当和毅力,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我也不止一次想象过自己终于站在东大殿前的心情。根据以往的“朝圣”经验,我以为自己会很了解此刻的感受:你左看右看,努力唤起并不存在的情绪。你试着对自己唱起颂歌:“XX在这里住过。”你说:“这就是伟大的xx事件发生的地方。”你说:“我站在他站过的地方,看着他看过的东西……”可并不管用。绝大多数情况下,什么都没有改变,理想中的感应并不会发生。也许这就是宗教朝圣和世俗朝圣的本质区别,我想,后者总是有可能让人失望,但你无法想象一个穆斯林会不满足于一生一次的麦加朝圣之旅…然而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了梁林所看到的——甚至还没有走近他们所看到的——我已经彻底被打动了。眼前的东大殿简直不像一座建筑,而更像某种自然力量,或是历史本身。从房檐斗拱,到大殿木门,乃至门前的古树和石经幢,都是货真价实的唐代原物。我之所见与80多年前梁林之所见几乎没有变化,与1100多年前落成时的变化也不算很大,甚至周围环境也几乎没有改变,一想到这里就简直要起鸡皮疙瘩。历史以真实的质感传递给你,你发现自己就站在1100多年前的时空现场,于是再也无法置身事外。殿外石阶前的经幢上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的字样,名列在诸尼之前。还有“大中十一年十月□□建造”的刻字,饱经风雨仍历历可辨。我看见有位僧人打扮的老者,不知是佛光寺的和尚还是管理员,正如数家珍地向几个游客讲解石经幢上的刻字。“看见了吧?”再次相遇时,老者关心地问。
“看见了,”我说,“不说确实看不出来。”
他满意地点点头,又一次露出笑意:“多亏了梁思成的远视眼……”
老者有一种淳朴沉静的神情,气质介乎村民和乡村教师之间,观之可亲,令我不好意思纠正他的错误——远视的不是梁思成,而是林徽因。正是林徽因以她的细心敏感,让所有人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答案。是她第一个注意到横梁下有淡淡墨迹,也是她第一个辨认出了梁上文字,又立刻去殿前经幢处详细核查姓名。两相印证,东大殿的建造年代这才确定无疑。
说是他的性别偏见恐怕有诛心之嫌,但女性学者的光芒往往被男性掩盖——即使他们共同参与同一项事业——这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实也不只限于学术界,女性经常在各种文本中缺席,她们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总是被男性角色所覆盖。令人欣慰的是,梁思成本人一向不吝于称赞林徽因的成就。就在发现东大殿的那一天,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个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妻子的珍重,那甚至是一种对作为整体的女性的尊敬。
梁思成把两位女子穿越千年的相遇视为某种宿命般的缘分。我看过一张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的“千年合影”,年轻的女建筑学家一只手搭在唐朝女殿主的肩上,肃然望向镜头,那画面的确有种不可思议的命运际会之感。面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里的宁公遇,林徽因似乎怀有一种既崇敬又亲近的感情。
“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她说,“让自己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身为女性的我忍不住猜想,林徽因之所以会与千年前的宁公遇产生某种情感联结,不只因为两人心中都有一份坚守的信仰或信念,也缘于一种同性之间的惺惺相惜——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漫长岁月里,她们都以自己的行动甚或存在本身,打破了女性仅仅是历史观察者的错误成见。
该说说佛坛上的那些彩塑了。
怎么形容好呢?我几乎整个人趴在铁栏杆上,既贪婪地看着它们,又简直舍不得看它们,因为心里明白这是一期一会的体验。
塑像在民国时期遭到俗匠重妆的厄运,三位主佛甚至还被画上了龙袍。重妆后的色调过于唐突鲜焕,失去了淳古的色泽。幸好塑像的形体轮廓尚得保存,而它们与我所见过的所有古代雕塑几乎都不一样,大概只有敦煌的一些塑像具有相似风格。它们高大健挺,面庞丰润,恬静端庄;尤其是佛前的胁侍菩萨,长眉入鬓,似笑非笑,腰部微微弯曲,姿态婷婷婀娜,简直有种妩媚娇柔的闺秀风度。这些女身菩萨头戴花冠,裸臂露腹,仅以披帛、斜巾之类遮蔽上身,且衣物自然垂贴于身体,逼真地表现出丝绸的轻薄质感,令人想起唐代崇尚的“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总之,它们既崇高又亲切,既庄严又世俗,既端重又柔弱,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微妙而和谐。大唐风流,宛然在眼。
真羡慕梁思成和林徽因啊,看到他们当年考察时漫步在佛坛上的照片,很好奇那会是何等奇妙的感受——仿佛行走在佛国仙林,还是回到了古都长安?
作为佛教雕塑艺术的门外汉,我常常看不出塑像的好坏——比如说,这一尊比那一尊更好,这个殿里的比那个殿里的更好——但当面对某些“特别好”的雕塑时,心灵似乎先于头脑有所察觉。当然,我能感到东大殿的塑像与众不同,却说不清它们究竟好在何处。我为眼前的佛菩萨震撼倾倒,但这种感情又仿佛与宗教无关。这些塑像并不需要任何宗教意义,光是它们外表所散发出的美、生命力与物质感,就已然赋予了自身某种道德力量,令它们光芒四射,穿越千年直击一个现代人的灵魂。
但我心中仍有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本能地感觉唐代的东西“特别好”?佛光寺乃无价之宝,自不待言,但大家似乎也都真心认为它很美——从建筑到塑像都美。然而我们究竟是以什么标准作出评判的呢?是纯粹的客观,还是一种被后天教化过的思想——大唐因其繁荣强盛格外令人向往,所以它的艺术审美也必然是极好的?
话说回来,我也知道艺术没有纯粹的客观。艺术离不开人,美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主观感受。我个人的直觉是:东大殿的建筑美感恐怕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感受,因其造型的简约大气和孔武有力正符合我们一向憧憬的大唐气度。而对唐代塑像的欣赏也许来自于将神的形象拟人化所带来的天然认同和亲切感。那种活泼浪漫的姿态,健康丰满的肉体感,无拘束不刻意束腰贴身的装束,以及因风气开放和民族交流而产生的异域风情(东大殿中某尊塑像完全是西域胡人的形象)……似乎统统暗合着我们现代人的审美。
谈到美,恐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我十分欣赏宋朝的清雅隽逸,但不得不承认,过于清简也会失去一些原始的生命力。我曾在陕西法门寺地宫的珍宝照片里看到一条武则天穿过的朱红色石榴裙,金光闪闪,华美无比,令人精神一振。石榴裙是唐代很流行的一种红裙子,古诗中对其多有描述——“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武则天将她最喜欢的石榴裙放在地宫中,意为代替自己供奉佛祖。一条红裙不仅仅是一条红裙,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那是一种热情奔放的生命力,也是一个时代繁荣自信的象征。
前段时间看了关于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或许也可以叫做《一位中国女性的苦水横渡与百年孤独》。一世多艰,寸心如水,叶嘉莹的传奇人生有太多值得讲述之处,遗憾的是导演对于内容的编排处理似有流于空泛之嫌——好吧,是空泛还是留白,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电影里充斥着缓慢唯美的空镜——山川河岳、亭台楼阁、碑文壁画……一切被导演认为能代表“古代”的意象。当镜头缓缓扫过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时,我愣住了。一些我似乎早该明白的东西轻轻击叩着心门,而我却一时找不到开门的钥匙,就像某个名字明明就在唇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迷雾忽然散开,答案凸显出来。它关乎唐诗与佛光寺之间的联系,也回应着我流连在东大殿时的内心疑问: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唐朝风物至美?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审美本身就来自于唐诗。
从学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孩提时代,到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年;从“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繁华盛景,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肃杀悲凉;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风流闲美,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淡泊清寂,从“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畅快淋漓,到“举杯销愁愁更愁”的失意苦闷……从风景到人情,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世界,唐诗所描绘的画面和意象早已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一套共通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密码——对月必然思乡,登高定要怀远,梅花代表高洁,杨柳暗喻离别,中秋叹“明月几时有”,下雪问“能饮一杯无”,村庄里“雉雊麦苗秀”,寺庙中“禅房花木深”——就连看到菩萨的细长眉毛,也不自觉地想到“懒起画蛾眉”……
就这样,唐诗(当然还有后来的宋词)润物无声地塑造着我们的审美和想象,指引着我们看待生活与世界的方向,也成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精神故乡。
我们天然是感性与诗性的民族,靠直觉去感受,靠隐喻去表达,靠意象去抒情。在与工业时代一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渐渐臣服于理性与逻辑,但那些诗句依然像伏笔一样埋在心灵深处。每当遇到某些特定的情境,尚未被理性驯服的直觉忽然被激发出来,沉睡已久的记忆被撼动了,缥缈不定的故乡如幻象般在胸中苏醒。我们带着怀旧的亲切感,回到那回不去的故乡:诗的国度。
所以我们怎能不为佛光寺所倾倒呢?它是故乡的月色。它是唐诗的现场。
佛光山如同天然的围墙从三面环绕着佛光寺。东大殿坐东朝西,独踞高台,背靠崖壁。站在殿前可以俯瞰全寺,前方山川河谷豁然开朗。那日天气晴好,云淡秋空,西天日光给东大殿镀上一层辉煌的金色。我们让毛衣站在殿前拍照,照片里一轮巨大的光晕笼罩着她,恍然真如佛光普照。
我隐隐感到,东大殿所处的高台是整个佛光寺的点睛之笔。它将佛光寺引入更大的山水格局,使得礼佛的空间超越了殿内,自然地延伸到下方的寺院,乃至整个山谷和远空。信众面对大殿则供奉礼佛,转身则面对自然与佛同观。两种观想禅定奇妙地合而为一,佛国世界与山水境界共同扩展到宇宙的尺度。敦煌观无量寿经变中有“日观想”图式——“正坐西向,谛观于日”;而夕阳返照,山谷幽深,正是东大殿前西望观想的真实写照。
东大殿明明是木结构建筑,却莫名地让人想起敦煌,除了塑像风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东大殿所处的空间乃是将山体部分凿开而成——凿出这块高台之后,再建大殿。大殿下方那排窑洞式的建筑,估计也是直接开凿于台基。而它的佛坛也是直接利用山岩劈凿而成,表层的砖下便是山岩。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石窟寺的变体,唐初的石窟便有在山岩母体之中凿出中央佛坛的做法;而当时的石窟寺,又有不少在洞窟外加木构屋檐。
据说佛光山岩中有一种五台绿岩,有将近30亿年的历史,是最早的陆地岩石之一。作为一座坐落在太古宙岩石之中的“石窟式”木构建筑,难怪东大殿会给人一种古老而奇特的时间感。
以前总听说佛光寺和日本的唐招提寺非常相似,实地造访后却觉得并非如此。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在京都、奈良旅行时的心情,起初是扑面而来的似曾相识与泫然欲泣,仿佛在异国找到了本土早已失落的唐宋氛韵——“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然而第一波冲击过后,似曾相识又渐渐变成似是而非——太完美了,太精致了,太顺畅了,太干净了。也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但总归是某些只能用感性体会而无法用理性理解的东西,令我感到这终究还是经过解剖化验后再“翻译”过去的大唐风韵。而正如某位诗人所言: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
来到佛光寺,才感觉一切都“对”了。或许也因为前两天刚拜访过五台佛国的诸多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风景历历重现;又来到台外这座货真价实的唐代原建,连周遭的山谷环境都未曾改变。眼前俨然是唐代社会的一个小小切面,或是凝结在时间中的一枚“唐代”琥珀,微小却完整,带着某种浑然天成、无法被“翻译”的拙劲与灵性,默默吐露着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
但它的完整和完美也令人惆怅。一枚完整的时间琥珀,一个完美的遗世孤例。在家国尚存而传统重伤的时代里,西风残照,佛光寺独立苍茫。昔日风流,而今安在?一股既亲切又遥远的哀伤弥漫在寺院里,仿佛来自一百年前或一千年前曾在此经过之人的心底深处——也许更早。
我们在佛光寺徜徉良久,也不知在看些什么,但就是没法离开。心满意足,又夹杂着丝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一种终极之感。地球上有些地方仿佛是临时之所,有些却亘古如斯地保存着它古老的精魂。隐没在山林之间的佛光寺,令我想起深藏在欧洲山谷中的一些修道院。当罗马帝国轰然倒塌,知识与艺术灰飞烟灭,欧洲陷入黑暗的深渊,那些依然醒着的灵魂撤退到乡间,然后以一种谦卑的耐心,一点点建起教堂和修道院——它们无法克服那个野蛮的世界,却能够延缓人类精神的瓦解。正是这些人建立了教堂,最终也再一次建立了欧洲。这个类比可能不算贴切,但对我来说,佛光寺就是这样的地方。当你抵达那里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触碰到了某种永恒与终极之物。你来到了地球上最好的地方——坚韧的灵魂居住之所。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逗留的时间超过了我们应该逗留的时间。该走了吧?我和铭基不断地说,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这样,我们在佛光寺的时间不断地被延长,等待着任何新的体验。每当我们想离开的时候,就会想起上一次想离开的时候,然后很高兴那股冲动没有被付诸行动。
后来,我们真的决定离开。走下那段陡峭台阶之后,毛衣又忽然反悔,说要回去画东大殿的斗拱。我和铭基立刻求之不得地答应了,感觉就像有谁借她之口说出了我们共同的隐秘心愿。于是三个人再一次爬上阶梯回到东大殿。毛衣坐在殿前的椅子上画画,我忽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便走进大殿去看个究竟。
是一位喇嘛正在诵经。他身着红色藏式僧袍,一只手不断摇动转经筒,口中嗡嗡唱诵不止。他身后是一小群藏人模样的信众,每个人都屏息凝神,虔敬地望向佛坛上的菩萨仙林。唱诵者只喇嘛一人,但大殿空旷,音节密集,他凭一己之力便营造出一种雄壮而庄严的气象。他唱诵了很久很久,久到连先前遇见的僧人模样的老者都忍不住进来探看,带着些许担忧怀疑之色,又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喇嘛的声音飘逸而郑重,我不知道他唱诵的是什么,也分不清词语什么时候变成了音符,四处滑行漂荡。它们还在不停地生长,如果被收集起来,就会无穷无尽。他的声音充满了信仰,但音符却延伸到更远,超越了一切。它们落在佛像的唇边,佛像似有笑意,仿佛在词语的边缘,却并不真正开口。于是它们继续飘行,又纷纷落在宁公遇的身上,宁公遇眉目低垂,神情谦卑,仿佛不相信自己值得如此的爱与奉献。我能感到,大殿里驻足聆听的每个人都在渴望成为那些音符,不是奉献的对象,而是奉献者。
我呆站在那里,感觉好似命中注定——我们注定要回来,注定要听到这仿佛来自古代的回声。喇嘛的声音不只是奉献,也是一种召唤,要把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精灵都召唤出来——精灵,或是鬼神,或是那些靠意会而非言传的美丽事物。这种召唤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东大殿仿佛在这一刻才真正活转过来,历史与当下发生了真实的关联,旧生命与新生命相互呼应,于是我们得以想象不朽。
或许这才是佛光寺的真正价值所在——不只是封存历史与国宝,更是对中国人心灵的慰藉。宗教是一种救赎,美和坚韧也是。而佛光寺恰好集所有于一身,让人相信无论历经多少劫难,世间仍有某种长存永驻之物。
最近看叶嘉莹记录片导演的访谈,他说讲到宗教性,中国没有“原罪”概念,可是在我们的几千年历史里,放逐、苦难、流离失所,所有这些,不管是在诗词文学、绘画创作,甚至像敦煌和龙门石窟的雕像里面,都隐约可以嗅觉得到。一点没错,我相信千年来无数有缘来到佛光寺的人们,都会动情猜想这漫长岁月里它究竟遭遇过多少险境;而在看完东大殿,转身面对悠悠空谷时,也都会一面为那庄严法相与山水胜景所震撼,一面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如何渡过苦水?怎样安慰生而为人的悲凉?或许还是要向那些美丽而不朽的事物中寻求指引。就像东大殿的斗拱,层层交叠,宏大雄健,承受着千年的重压和委屈,却仍不失纵横恣肆之势;就像我们都热爱的唐诗,在格律最严谨的时候,反而产生了最自由最辉煌最具超越性的创作;就像梁思成笔下那些隽永的文字,将当年野外考察时的千难万苦,都化为一种追求理想的至乐……它们并不提供答案,但其存在本身犹如水中浮木,令我们的心有枝可依,带着不该活下去的感觉而活下去。无论长风破浪会有时,还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一同在苦水里颠沛沉浮,看尽所有,哀而不伤,从容不迫。
五台之行犹如一场寺庙巡礼,又像是寻宝游戏。“地上文物看山西”,这片干旱而神秘的黄土地实在隐藏着太多宝藏,多到想要一一妥善保护都有心无力。
佛光寺之后,我们又接连看了四座体量较小的古庙,都不算出名,却都不虚此行。每一座都隐于平凡无奇的县城或乡村中,几乎已丧失了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荒芜萧索,游人寥寥,但这反而产生了某种戏剧性——你不无疑虑地推开朴素的寺门(有些甚至需要自己把门敲开),然后被眼前的稀世珍宝震撼得哑口无言,那样的反差好似明珠之于河蚌。
想象中的审美疲劳没有机会发生,因为每座寺庙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戏剧性。洪福寺以造型取胜——它俨然是座土堡,被十余米高的夯土高墙所围绕,据说是为了防范蒙古兵的侵扰。看门的大爷自顾自在厢房里刷漆清扫,完全懒得搭理我们。但当我敲门要求参观正殿,他也一声不吭地拿上钥匙给我们开门。正殿是宋末金初遗物,里面是灿然满堂的宋金风格塑像,秀美而灵动,比佛光寺的彩塑更像“汉人”,梁顶还有一组小而精致的飞天乐伎。我们如饥似渴地看着,而看门大爷就拿着钥匙站在一旁等待,并不催促,但令人颇感压力。铭基拿出一张钞票放在供桌上,大爷没有说话,但你能明显地感觉整个气氛陡然一转,于是我们得以安心从容观看。离别时大爷匆匆向我们走来,把一个巨大的石榴塞到毛衣手里,依然沉默少言,但微笑像池塘中的波纹在他靴皮般的脸上荡漾开来。
广济寺大隐隐于市,藏身于五台县城的一条热闹街道。实际上它如今仅存一座大雄宝殿,有些尴尬地与文管所和博物馆共处同一院落。我们懵然不得其门而入,被拴在一旁的看门狗以一种无比凶悍的态度狂吠不止,如果没有那条绳子,它估计已经把我们统统撕成碎片。手足无措之际,文管所的一个男人说钥匙在打扫的女人那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女人,又好不容易搞定了当地的健康码,终于被获准进入。女人不断叫着看门狗的名字试图喝止它,但它对我们居然被批准进门这件事感到无比愤怒,愈发张牙舞爪,蹦跳狂吠。我向它投去一个“老娘赢了”的眼神,从前院一侧的墙根穿过一个小门洞,眼前赫然是另一个世界——大雄宝殿立于宽阔的台基之上,恢弘而静谧,将现代社会彻底隔绝在外。大殿是元代遗构,中间四根檐柱都饰有造型奇特的兽头:独角兽居中,两侧的似乎是长着鹿角的龙头。更特别的是转角处檐墙上站着两个穿肚兜的小人,年画娃娃般趣致可爱。与外在的局促凋零相比,殿内的元代塑像保存之完好令人惊讶,连佛像身后的火焰纹都依然鲜艳夺目。我们在打扫女人的陪同下,缓慢地绕着佛坛转了一圈,从各位栩栩如生的菩萨、罗汉、狮、象前经过,全程屏息静气,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南禅寺是国内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比佛光寺东大殿还要早75年。由于它只是个乡村小庙,等级和规模都远不如东大殿,但仍能一眼看出两者建筑风格的相似——屋顶举折平缓,斗拱粗壮朴实,都是典型的唐代特征。殿内的佛坛塑像也都是唐代原物,虽不如佛光寺的精致,但也是如出一辙的雍容大气。南禅寺出过严重的盗窃案,如今仍能看见被锯断的塑像的两个脚跟残骸,短短地立在地上,令人心痛。毛衣对这一点尤其在意,盯着看了很久,还反复地让我给她讲被盗始末,不知究竟是愤慨于盗贼之猖狂,还是对具体的犯罪手段感到着迷……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延庆寺。它也是座村庙,如今只剩一座金代大殿,看以前的照片连围墙都没有,完全裸露在村口,一片颓败荒芜。如今寺庙已被重新修缮过,多了钟楼厢房等新建筑,但那座大殿的气场与它们完全割裂,默默散发着幽微难言的骄傲与寂寞。作为全然的外行,我说不清为什么特别喜欢这座大殿的外形——是因为屋脊的优美弧线?还是两侧厚而倾斜的夯土山墙?或是殿前肆意生长的秋英和孔雀草的衬托?最直觉的感受是它像某一类男子或女子,并非令人惊艳的绝色,却格外典雅耐看。
那时已过午饭时分,我们也无法进入殿内(从窗缝中窥视,里面也不过是俗陋的全新塑像),但在佛光寺曾一再感到的留恋之情又一次袭来,把我们牢牢按在原地。毛衣拿出了绘画本,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临摹大殿中间两根檐柱上的兽头装饰。它们的原型大概是龙或龙的某个儿子,头上的长角已在岁月沧桑中断折,但仍鼓着眼睛,龇着牙齿,誓要吞下这难以下咽的檐柱。它们也凶巴巴地盯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仿佛一位性情乖戾的主人被打扰了午睡,但又因为这难得的关注而心下窃喜。技艺精湛的古代雕塑家驯服了这些异兽,将它们变成石头或木头,它们又反过来驯服了游客。
天空开阔,四下寂静,只能听见风吹过孔雀草、蜜蜂停在秋英上的声音。除了我们三个,再无旁人。我本以为这座寺庙的荒凉幽静会令它成为更具灵性的场所,显然错了;但又很难得出结论说它已被遗弃,或是彻底丧失了能量。这不过是座古老的荒寺,像一座既不活跃也没有死去的火山。它依然美得令人心折,也因此依然保有生命,发出微小的光,为自己带来一些什么。
我在延庆寺里走来走去,怀着某种难以置信的紧迫感,努力把每一帧画面都摄入眼底:寂寞的金代大殿,正在画画的毛衣,粉色的秋英与金黄的孔雀草,村民铺晒在廊檐下的满地红枣……紧迫感关乎当下的拥有,而非永久的保留。因为心里知道我们无法保留任何事物,因为记忆很快就会遗失,甚至连我们自己也终将被时代抛弃。“你知道吗妈妈?”五台之行中毛衣总是重复说着同一句话,“现在也是过去。”我不会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但她道出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我需要用心咀嚼这一刻,需要确知自己在场,甚至需要写下这长长的文章。为了存在,为了记忆,为了见证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
行前做功课的时候,我和铭基常有犹疑不定的时刻:xx寺值得去吗?xx寺是否太远?如果不开门又怎么办?然后,从第一座寺庙开始,这些问题早已烟消云散。寺庙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这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事实。
在延庆寺里,我想起了一首诗,来自我非常喜爱的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
“金斯堡有一天下午来到我屋子里
说他准备放弃诗歌
因为诗歌说谎,语言失真。
我赞同,但问他我们还有什么
即使只能表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抬头看星星,而它们
并不在那儿。我们看到的回忆
是它们曾经的样子,很久以前。
而那样也已经绰绰有余。”
面对那些近乎永恒又注定消逝之物时,在心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最终触到的只是一点点脆弱的联系——“而那样也已经绰绰有余。”
=========照片的分割线========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