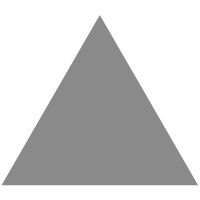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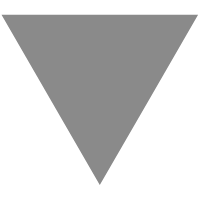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第 42 期:袁卫教授
source link: https://cosx.org/2021/12/interview-of-yuanwei/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简介: 袁卫,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委员,国际统计学会(ISI)选举会员。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曾任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应用经济学评议组召集人,第七届统计学评议组召集人。
图 1:袁卫 2021 年国庆节在山西大同
本次访谈由统计之都组织,王小宁、任焱、孔令仁、王祎帆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对袁卫老师进行面对面采访,邱怡轩线上接入,之后赵昊蛟、王小宁、李舰、魏太云进行了文字转录、校正、整理和精简,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文字中加了小标题,文中图片由袁卫老师提供。下面是访谈正文。
求学和工作经历
统计之都: 首先请您介绍下个人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袁卫: 我的经历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50 年出生,住在什刹海后海,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算是个老北京。我的中学是北京 101 中学,当时我们家离北京四中比较近,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平时在单位住,他们没时间管孩子,我奶奶又有心脏病,后来父母亲商量,说为了家里清静,上中学时让我去住校。我考 101 中就是因为 101 中远一点,多数学生是可以住校的,要不然的话北京四中或者北京八中可能是我会读的中学。
图 2:袁卫 1969 年在中山公园(过期胶片洗印的彩色照片)
接着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我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找了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开始照相玩摄影,这完全是偶然的事情,后面谈爱好时我会说细点。接下来上山下乡,我是 68 年 7 月份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与插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兵团是半军事化管理,吃的会比插队好,又因为东北是国家的粮仓,我们吃的还是挺不错的。插队比较自由,但要挣工分,所以插队有的时候会有吃不饱的情况。那个时候插队的几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愿意看什么书、愿意想什么、讨论什么都没关系。我们在兵团都是住连队的大帐篷、大通铺,一个房间好几十米长,过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读的只能是允许的图书,比如《毛泽东选集》、《资本论》等。
去兵团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个锻炼。去兵团三四年以后,大家就开始思考是不是一辈子要在这儿扎根,刚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去想自己后面会怎么样。国家号召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就响应,别人能吃的苦我们也能吃。当时还是半军事化管理,个别身体不好的能开出特别重的病假条,按照政策可以返回城市,我们把这叫做病退。后来有一个政策,一个家里有多个孩子的,北京允许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如果孩子都走了,可以有一个返回城市照顾父母,这叫困退。按照国家规定,只有这两种渠道回城市,一个是病退,一个是困退。
从 1970 年开始,部分地区恢复高等教育,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刚开始还有一点文化的考试,后来出了白卷先生张铁生,就完全没有考试了,基本上都是推荐。上大学既可以学知识,还是名正言顺地离开兵团,当然是最好形式。我在 75 年的时候也被推荐上大学了,最开始的时候团里说送我上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读书。我在黑龙江干得不错,提了排长、入了党。当家里人得知我可能回北京上学,还是挺高兴的,但在 1975 年 8 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是牡丹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我还是还挺高兴去的,因为毕竟能去读书。
图 3:1979 年袁卫(左三)兄妹 5 人在后海,从左到右从长到幼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全都上山下乡了,我是老三,前面四个都是男孩,最小的妹妹在北京郊区插队,也算上山下乡。按照刚才说的,我们家有一个困退的名额,妹妹反正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弟弟已经工农兵推荐上清华了,我哥哥在山西插队比较近,只有我离家最远,所以父母就希望我回来。而且他们说在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毕业后,只能留在牡丹江地区当中学老师,基本就回不了北京了,他们希望我能够利用家里这个困退的名额。
恰在这时燃化部大港油田招工,部里的职工子女,包括上山下乡的子女,都可以申请,这样可以帮助部里和直属单位的职工解决子女回京或者回到离家较近的天津,我就利用这样的招工名额到了大港油田,这时是 75 年底。从 1975 年夏我拿到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当年 12 月我退学、退回兵团,又从兵团 6 师招工来到燃化部劳资司报到,整个的手续都是我自己想办法,也可以说是闯出来的。由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 师地处建三江,是在珍宝岛附近,兵团 6 师拒绝燃化部的招工,不放人。当燃化部劳资司领导正为十几个 6 师知青办不出来着急时,我拿着 6 师的调令回到部里报到,司领导非常惊讶。他们听完我的故事,认为我办事能力强,直接分配我去大港油田政治部干部处。一般来讲干部处干事都是在油田基层锻炼十年八年的人才能够去管干部,我一到那儿就去管干部,在机关我就有了较多的业余时间,开始自学。
上大学读书
1977 年秋恢复高考。我之前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但没去,心中一直有个读书梦,非常渴望能够有机会多读点书。记得从国家公布招生政策到考试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完全不知道考什么,但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读书的愿望,只要能有机会读书就已经足够了。报名时我自己判断了一下,因为那时候还有老高中的考生,他们的中学基础训练比我要扎实。我报名的时候,由于没有学过高中的物理化学,本来想去学摄影,但没查到相关专业招生,就报了文科,因为文科考历史和地理,相对比较容易。
我在大港油田的两年里,业余时间学了点儿日语,每天听广播学半个到一个小时,当时日语还算是有一点基础,就填报了日语专业。能够选择的是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第三志愿报的是天津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有一个外贸系,录取外语类,但没有注明外贸系是录取英语、日语还是其他语言。当年高考时我已经 27 岁,外语类录取标准原则上是 25 岁以下,日语最后考试的成绩中等。因为我的年龄超龄,所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的日语专业都没录取,天津财经学院看我的总成绩还可以,工业统计专业报名的人很少,就准备录取我。
记得我正出差到河北宣化干部外调,接到了油田转过来的电话,说天津财经学院想录取我到 “工业统计” 专业,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们就发录取通知书。我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把名额给别人了。我当时对于什么专业,想都没想,痛快地答应了。从 68 年去兵团到 77 年底,快 10 年了,越来越渴望读书,不管是什么专业, 只要有书读就行。我在兵团的时候,知道每一个连队都有两个特殊岗位,一个是会计,还有一个统计。统计员负责丈量连队有多少土地。由于很多地块有树林、有河流、有水泡子等,是不规则的多边形。如果要准确地计算几万亩地的面积,就需要统计员,最后还要计算平均每亩的粮食产量和收入等。当时我猜想,统计可能就是干这个,肯定有知识可学。就这样,我进了天财的 “工业统计” 专业。现在想一想,在大学里以 “工业统计” 作为一个专业,比较窄,这是计划经济的烙印。
进入大学后,专业课一般从 “统计原理” 开始。我们国内的统计学分成了经济类和数学类的两种统计专业,天财是经济类的,最后授予经济学学位。当时经济类统计学专业最好的是人大,南方的厦大也不错。我希望能通过考研去人大,去接受最好的统计教育。我们 77 级入校已经 78 年年初了,79 年时还允许在校大学生直接考研,不管你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学生。1979 年我刚入学一年多,就考了一次人大的研究生。由于统计专业课是在二年级以后才学,因为没学统计专业课,所以我不敢考统计专业,就报考了人大 “工业管理” 专业。工业管理这个专业主要考经济和管理理论,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感觉去找点书好好看看就可以,最后我的英语、政治和数学成绩尚可,但专业课不及格,否则我在 1979 年就进人大读研了。
这次考试的时候我刚上大二,虽然没考上,却增加了我考研的信心,觉得只要努力的话,肯定能考上人大。大学毕业时考人大比较顺利,进人大先读了三年的硕士。第一批博士点是国务院学委会按照人来设点的,只要有一个很强的教授,不管这个学校是北大、清华还是其他学校,只要他的资历和学识足够就行。1981 年人大博导共有 9 位,包括肖前、宋涛、吴大琨、戴世光等。人大的统计专业是第一批经济类的博士点,博士生导师是戴世光教授,也就是我后来在人大读博的导师。
图 4:1981 年 5 月美国统计学会会长 Breadley 率团访问中国,方毅副总理会见。 前排左起 J.Press、戴世光、Beadley 夫人、李成瑞、R.A.Beadley、方毅、F.C.Leone、M.E.Muller、王一夫、V.Tsou、王寿仁
我的大学读了 4 年,接着读了 3 年硕士,3 年的博士。1984 年底我在人大硕士毕业后已经留校当老师了,博士生阶段是在职攻读。博士的三年我们一边教一点书,一边完成博士论文。我们这一届三个人,任若恩、蔡志洲和我。1988 年初,我们答辩通过,成为我国经济类首批统计学博士。
担任人大统计系主任
1992 年元旦,我们系主任韩嘉骏老师因突发心梗,人一下就没了,非常突然。学校在这个月 15 号就让我当系主任。1992 年到 93 年对于经济类的学科是一个低潮期,因为 92 年我国核算体系有一个转型,现在上课都是 SNA 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从改革开放后到 92 年,实际上是 MPS(Material Product System,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就是原来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主要差别在于服务业算不算生产性劳动。我们当老师的、当演员的、从事家庭服务的等,在 92 年之前这些服务行业的劳动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都不算生产性劳动。当时经济核算的范围,只有工人、农民、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的劳动才创造财富。
我们原来经济统计的教学主要是学苏联的,围绕着计划经济体系设置课程。国家的宏观核算体系变了,我们的教材当然也要改变,老师要讲新的、联合国通用的 SNA 体系。与此同时邓小平南巡,讲了很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话。财经类专业怎么适应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一时间,社会上将带有 “国际” 二字标签的专业误认为就是国际化了。导致一些高校开设了很多奇怪的新专业,如国际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结果是,一听说有 “国际” 二字,就认为这是一个高大上的专业,录取的分数也高,学生报名也踊跃。我们统计专业在当时面临不少困难,一是国家核算体系变了,怎么适应?我们人大统计专业一直以培养国家统计系统的专业人才为己任,包括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局等;二是,社会上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误解,认为只要挂上 “国际” 就是国际化、并以此吸引学生报考。1992 年初,我接任系主任时,深切地感觉到我们原来的统计教育已经不弄满足国家改革开放对统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必须改革。但怎么改?困扰着我。
在我当系主任之前,一直和一位老师保持联系,他就是张尧庭先生。张老师原来是许宝騄先生的助手,许宝騄是我国数理统计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一人。张老师北大毕业,50 年代做过许宝騄的助教,文化大革命时被分配到贵州,再到武大。1985 年,在国内由张尧庭主持的赴美留学全国招考派遣项目正式启动,每年从各校推荐的 100 名硕士毕业生中选拔 30 名,在美国由刁锦寰先生等推荐赴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经该项目先后送到美国的留学生中,多人已成为当今国际统计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记得回归分析课在人大教学二楼(现教三楼)4 层的教室上,40-50 人座位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张老师讲课神采飞扬。正因为这个关系,张老师受聘成为我们的客座教授。1987 年我还没有博士毕业,学校就任命我当了系副主任,负责学术交流,和张尧庭老师接触越来越密切。我当系主任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张老师请进来,学校先给了他一套房子,引进的相关工作都很顺利,但最后因为张老师的户口进北京的问题,被北京市卡住了。当年北京市规定,进京落户人才的年龄不得超过 58 岁,张老师刚好超过。就因为这个年龄问题,张老师的引进没有办成。但因为在人大校内有一套住房,张老师每年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在我们这儿开课。
图 5:袁卫(左一)、刁锦寰(左三)、张尧庭(左四)、易丹辉(左五)在人大图书馆前,1994 年
1992 年初,在我接任系主任后,正为如何拓展我们的学科领域发愁时,张老师跟我说:人大财经有优势,统计有一个方向叫 “精算”,是概率统计与金融和经济的结合,或者说是概率统计方法在风险管理与保险中的应用。我之前没听说过这个方向,经张老师一点拨,赶紧查阅相关资料。意识到精算学科可以用概率、用统计来解决金融保险风险等问题,是我们统计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段开龄先生在 80 年代后期首先将北美精算教育和精算师考试引进中国,本来段先生准备将第一个美国精算师协会支持的研究生项目设在人大,但由于当时人大的领导没有及时表态,第一个硕士班就设在了南开大学。我为此在 1992 年上半年专程去天津南开大学取经,遗憾的是空手而归,不得不再想办法。
刚好在这个困难时候,学校有一个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简称 CIDA)的交流项目,我们人大与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是对口合作院校。麦吉尔大学是蒙特利尔的一所老学校,在加拿大大学中综合实力排在前三。我立即向学校申请,想利用短期访问考察北美精算教育的情况,并尽快引进精算教育,培养我国的精算人才。1993 年 4-6 月,我利用在麦吉尔的三个月访问时间,联系了北美精算师协会,拜访了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 “统计学与精算科学系” 的 Sharp Huntington 和 Robert Brown 等名教授,得到了一批宝贵的教材和教学资料。回来后,很快我们的精算本科专业、硕士和博士方向就上马了,当时北美精算师学会要在中国布考点,北京的考点还没设。在与北美精算学界建立联系之后,得到了北美精算师学会不少帮助,北京考点从 1995 年就设在人大。他们的会长每年换一位,每一年的会长上任后都来中国,每到北京,必定访问人大。北美精算师考试的考试费对在校学生来讲,是不小的负担。我们得到瑞士再保险、美国纽约大都会保险、澳大利亚安宝集团等大力支持,培养了一大批精算人才。
我当了系主任之后,觉得自己的视野不够,经验不足,希望能出国访问增强阅历和能力,学校非常支持。1994 年,我向学校申请美国富布赖特项目,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去美国名校进修一年。富布赖特项目与其他访学项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项目是美国政府主导的。富布赖特项目的设立,最初是二战后美国富布赖特参议员建议将二战剩余的美国战略物资就地处理,筹集经费用来促进美国和世界的学术交流。学校支持,我也顺利地通过了美国大使馆的口试。
在选择进修的美国学校时,段开齢教授建议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沃顿商学院(Wharton),因为美国名校中只有沃顿有风险管理和精算系,是当时美国最好的。那一年我就在沃顿上了几门风险管理和精算的课,最主要任务的是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把他们考试的资料带回来,这是我的访学经历。
担任人大副校长
回来之后,我原准备全力投入到精算教学与研究,但不久学校就任命我当了副校长。我从 1997 年到 2004 年,当了 7 年的副校长,然后又从 2004 年到 2012 年干了 8 年的常务副校长,这 15 年主要的精力和工作是学校的管理。学校工作的后期,我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到了统计学史上。
统计学史研究
出发点:中国统计学史研究的缺位
统计之都: 是什么驱动您转向统计学史的研究呢?
袁卫: 我这个研究兴趣最早受了两个刺激。第一个事儿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有一个纯美国人,历史系博士生。他对人民大学在建国之初的历史感兴趣,就以这段历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我看到他的论文后,很震惊,他的研究视角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他是从学科史这个角度来写的。在本世纪初,资料获取还是比较容易的,他来到我们图书馆,图书馆觉得老外来研究我们也挺好的,对他开放。学校办公室把它翻译成中文,作为校史的一部分。
论文的题目是 “建设社会主义大学——中国干部与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与实践(1949-1957)”,内容主要是中国高校,特别是人民大学怎么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办学,写了办学的探索和经验。刘少奇在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大会的讲话里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人大怎么办,将来我们中国大学就怎么办。朱德强调人大要学苏联,学莫斯科大学。人大在 50 年代的办学体制、办学经验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些研究党史的人会感兴趣,但从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是很有特点。看完论文,我在想,我们人大有很强的党史和历史学科,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自己的特殊历史没有兴趣,没有下那么大的功夫研究,反而让一个外国学生、让一个跟我们不太有关系的人来研究?
第二个事儿就是统计了。关于统计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若干本叫做《中国统计史》的书,有刘叔鹤、李惠村、莫曰达等的几本,主要是政府统计工作或者是统计活动的历史,至今没有一本《中国统计学史》。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印度裔博士生,中文名字叫郭旭光,英文名是 Arunabh Ghosh。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由于对上世纪 50 年代中印统计交流感兴趣,就以 50 年代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统计事业为题,完成了 “Making It Count” 的博士论文。这个题目、这个书名很难准确地译出中文,论文内容讲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运用数据,怎样通过定量(count)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就是讲 50 年代的统计史。
图 6:Arunabh Ghosh 的博士论文(左),2020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袁卫和 Ghosh 在办公室交流(右上、右下)
50 年代已经到了当代中国,这本书的一个视角是从统计这儿深入的,需要了解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其他的事情,他也主要凭着这项研究,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的教职。这本书在印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讨论,现在郭旭光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哈佛大学有三个历史系,一个一般的历史系,一个建筑史系,一个科学史系。记得是 2011 年 9 月的一天,学校办公室跟我说有个老外来找我,说他对我们 50 年代统计史感兴趣,要见我。我在办公室接待了郭旭光,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中国 50 年代统计事业的博士论文,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去采访吴辉、龚鉴尧、林富德和倪加勋。我得知他为此先在美国学汉语,然后又到北京待了两年,在清华一边学汉语,一边搜集资料,整个研究历时近 8 年。
印度有好几位世界级的统计学家,C-R Rao 大家可能都知道,还有一位叫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马哈拉诺比斯 1931 年在印度办了一个统计学院,简称也是 ISI(Indian Statistics Institute)。郭旭光对中国统计史感兴趣,重要原因是他是印度裔,50 年代中印的统计交流曾经有一段是蜜月期,大概在 56~58 这三年时间。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中国来,周恩来总理两次去印度,而且也到了马哈拉诺比斯的统计学院。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虽然有抽样的概念和方法,但不是随机的,而是主观的、任意的,带有典型调查的意思。由于没有随机的概念,当时抽样很难准确地推断总体。
图 7:1957 年 7 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马哈拉诺比斯等人(左起:翻译、尼赫鲁大使、拉希瑞、邓颖超、马哈拉诺比斯、马哈拉诺比斯夫人、周恩来、尼赫鲁夫人、薛暮桥、王思华)
当时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宏观管理上遇到的问题是,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农产量、家庭收支等的变化如何比较准确地推断和估算?按照苏联的模式,国家领导层觉得不准。当周总理访问印度时,马哈拉诺比斯告诉总理,说通过用随机抽样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推断农产量,和家庭收入情况。周总理印象深刻,回来就跟时任统计局长薛暮桥、副局长王思华说,你们要去考察考察。50 年代我国和欧美没有任何外交和学术联系,当时是冷战时期,仅有的国际交流几乎都是面向苏联和东欧的,唯一的一个特例就是印度。印度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但印度又是我们的邻居,而且在国情上又与我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再加上当时尼赫鲁比较开明,50 年代中印有过一段蜜月期,如组织万隆会议一起来为亚洲做事情。周总理 1956 年访印不久,我国派了一个统计代表团去学习考察,代表团只有 4 个人,王思华副局长为团长,包括我的老师戴世光。
这次访问持续近一个月,重头戏是 12 月 20 号印度统计学院院庆和学术报告会。印度统计学院是 1931 年创建的,1956 年是 25 周年的院庆。那次院庆马哈拉诺比斯凭借他的影响,请了一些国际统计大师,如美国的 Neyman,英国的 Fisher。中国代表团作为政府代表团,是尼赫鲁总理的客人,受到了热情接待。20 日上午的大会报告人包括 Fisher、Neyman、Yates、王思华和戴世光等。王思华讲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工业怎么和农业相结合,戴世光介绍中国 1953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Neyman 的报告题目有意思,讲的是 “统计学是所有科学的仆人”(Statistics is a servant for all science field),统计学如何为不同学科提供服务的题目,非常吸引人。Fisher 的报告是 “科学研究中的概率问题”。大家都知道 Fisher 和 Neyman 两位大师,早在 30 年代伦敦大学学院时就在一栋小楼里,由于学术上有分歧,个人关系上也有隔阂。他们二人留下来的合影照片很少见,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 1956 年底,在印度统计学院与马哈拉诺比斯三人的一张合影。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中国代表王思华、戴世光等与他们的合影。
图 8:1956 年 12 月印度统计学院院庆学术报告议程
1957 年,应国家统计局的邀请马哈拉诺比斯来到中国,实际是周总理的邀请。他在人大做了两场报告,一场报告是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偏科普性质,第二个报告是 “抽样调查”。
郭旭光以中国统计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件事儿给了我又一个极大的刺激。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高校,没有一个人去做深入研究,而是让远在地球那边的一个外国人来研究,身上有种被刺痛的感觉。从那时开始,我下决心在退出行政岗位后全身心地投入,写出一本中国统计学史来。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学者叫白安雅,她研究中国数学史,也研究中国的概率统计史,她从 90 年代就开始研究,一直到前几年我们接触,她对我说她终于找到一个中国统计学界对自己历史感兴趣的人了。
研究目标:填补中国统计史空白和纠正谬误,启迪后来人
我之所以要编写统计学史,首先是要填补统计学的空白。比如,统计学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任何记载,早在 1912 年,即民国初年,交通部司员曾鲲化就写报告获批举办 “统计学堂” 和“交通统计专业”,共 20 门课,这比 1911 年 K.Pearson 在伦敦大学学院创办 “应用统计学系” 仅仅晚了一年;再比如,统计学界过去没有人知道,吴定良 1926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后,转学到伦敦大学学院,师从 K.Pearson, 1928 年获得博士学位,在 Biometrika 上与 K.Pearson 等合作或单独发表 11 篇论文,是国际知名的生物统计学家。这样的例子很多。
除了填补空白,还有就是纠正谬误。过去的几本统计史书,几乎是抄来抄去。前人这么写了,后人没有查阅原始资料或文献,照抄照编。比如几本统计史书上都说,早在孟森翻译横山雅男《统计通论》(1908)之前,1902 年钮永建翻译了横山雅男的《统计讲义录》(中华书局);林卓男同年翻译了横山雅男兵库县印发的《统计学讲义》(时中书局)等,所有文献和研究论文都说没有看到图书的实物。 我们最终从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传说的原版,实际是林卓男 1903 年翻译(钮永建校)出版横山雅男日文版的《统计学讲义》,中文译名为《统计学》。(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古籍资源库唯一一本藏书,清光绪 29[1903] 年,上海时中书社发行)。
我们编写《中国统计学史》的原则是 “全面、客观、准确”6 个字。我们统计学的历史并不长,真正作为学科也就是 100 多年的时间,清朝末年通过日本引进。“全面” 要求我们尽可能搜集到 100 多年来所有的统计出版物和相关文献,先要找原版,实在找不到原版的,再考虑电子版。每本书都要从头到尾认真阅读,所有的序、注,都认真研究。翻译的著作,要和英文的原版对照。这样,清末民国统计出版物约 400 本,我们几乎收齐了。“客观”要求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现状,尽量引述原文,尽量减少用现在的观点加以评论。“准确”要求我们工作细之又细,出版的时间、版本的辨别,以及内容的研究都要非常严谨。
做统计学史研究一是靠责任感,二是要有兴趣来驱动,而不是任何利益的驱动。我的兴趣部分来自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完成这一历史责任,带有抢救性挖掘的性质。研究学科历史要耗费大量时间,对我来说从准备开始到现在已近 10 年,全力投入也差不多 5 年了。如果从利益的角度,统计史研究很难发表论文。在学校博士生招生目录上,我一直注明研究方向 “中国统计学史”,但基本没有人报名。显然,研究统计史,博士学位没有 6、7 年时间不行,毕业了也很难找到工作,更挣不了多少钱。欣慰的是,学校里还有几位老师很感兴趣,确保我们团队能够在明年完成初稿,争取后年与读者见面。
统计之都: 我国统计史上重要的学者有哪些?
袁卫: 我国第一位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统计学者,过去一说就是许宝騄。但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在许宝騄之前还有吴定良先生,吴先生做生物统计,与 K.Pearson、F. Galton 做的优生学、人体测量,都是用统计方法。最近研究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我们梳理一下,发现民国从 1920 年到 1945 年竟然有 33 位留学生在欧美做理论和应用统计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人数就更多了。陆志伟、陈达、艾伟、袁贻谨、唐培经、徐钟济、厉德寅、金国宝、戴世光、邹依仁等的故事都很感人,1948 年首届中央研究院 81 位院士中,竟有 4 位统计院士,分别是陈达、吴定良、袁贻谨和许宝騄。
统计之都: 您之后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开设统计学史课吗?
袁卫: 我跟学院说了,可以在学院开一门选修课,学院还没给我回复。我现在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把统计学史写完、写好。统计学史完成之后,我还准备写一本人物卷,主要是讲统计人物的故事。同时,我这 10 年收集了许多统计老物件,比如 1897 年我国第一本概率论译著《决疑数学》、1908 年孟森翻译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大量民国统计出版物等,我有许宝騄先生 1950 年在北大亲笔书写的开设 “分析讨论班” 和“实变函数”课程计划,以及朱祖晦、吴景超、徐钟济、薛仲三、江泽培、魏宗舒、王寿仁、成平、陈希孺、陈家鼎等统计名家的手稿和信札。将来,我会办一个中国统计学史的展览,用这些珍贵学术文物启迪后来人。
统计学发展和教育
统计学的发展
统计之都: 统计学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了,您能讲讲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吗?
袁卫: 统计学整体,作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并列的学科,在国外没有问题。中国的学科为什么要强调它是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因为我国的资源是按照研究生目录的一级学科来配置的。现在学科评估对各个学校来讲都很重要,你排在 A 还是 B 直接关系到经费和地位。一所学校对外宣传有几个一流学科,直接关系到声誉、招生和经费等。在现阶段,一级学科就是配置资源、进行评估的基本单位和标准。一级学科对统计来讲,姑且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十几年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学科还是分散的,一部分是数学下边的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数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另一部分是经济学下边的 “统计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医学门类里面还有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在国外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文理学院里的统计学,基本上就是数理统计方法和应用,另一类是几乎所有名校都有的生物卫生统计,基本都是在医学院或者公共卫生学院里。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名校,生物统计系的老师往往比文理学院统计系的老师还要多,因为医学和健康太重要了。国内按照一级学科来配置各种资源,一级学科涉及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现在我们争创世界一流学科也都是按照一级学科目录安排的。由于一级学科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竭力将统计学合并为一级学科的道理。当然,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争取资源,而是要建设好统计学科,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为国家服好务。
同学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我们有许多年轻人去欧美学习统计,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统计学系中都有来自于大陆的老师。其中优秀的代表有郁彬、范剑青、孟晓犁、何旭铭、刘军、林希虹、蔡天文、寇星昌等,他们都是从国内高校数学系出去的,数学基础扎实,到了美国受到系统的数理统计的训练,特别是联系实际,就做得如鱼得水。在整个统计学科,数学、概率和数理统计是基础,应用到生物、心理、教育和经济等不同领域后当然有不同的特点,我们通称为应用统计,每一个领域都不一样,方法的侧重点不一样,好的学科一定要有很扎实的基础。我们如果没有一级学科,各分支就容易支零破碎,当然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研究应用。
尽管现在统计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但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继续扩展,更名为 “统计学和数据科学”,会更适应大数据时代。当然,统计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或方法,数据科学绝不仅仅是统计一家就能够独立把它支撑下来,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学科,如计算机等,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自然过程。同学们要跟上这个时代,一定要学好包括计算机、统计和数学等学科,把基础打得扎实一点。
统计之都: 人大现在有统计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信息学院和大数据研究院等,都在做数据科学相关研究,您如何看?关于未来的数据科学发展趋势,是否需要统一培养?
袁卫:现在的学科会越来越交叉,早期事物的度量相对比较简单,用简单的方法,在一个学科领域,能够把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但现在我们的度量越来越精细了,记录也越来越精细,不仅仅是通过一个侧面来度量,可能还需要横着度量、纵着度量,比如照相,过去就是一个角度照相,现在利用无人机,可从上面甚至转着圈来照,所以观察同一件事可以从不同维度来测量。人们认识社会,已经不能简单地从一维或二维来看,很多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变化的过程。从培养人才来讲,一定也是这么一个趋势。
历史上,以中国的国学为例,研究分得没那么细,文、史、哲、语言学等都在里边,后来受西方影响,文、史、哲、数、理、化越分越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学科分得越细,越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问题可以这样,但要解决问题,对于解决综合的问题,光有深度是不够的,还得有一个互相的联系。要解决一个系统工程,比如教育改革,我们 “双减”,减轻孩子的课外负担是好的,但导致学生负担重的根本问题不是把课外班减少了就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很复杂,孩子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简单的一刀切未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有一套办法,如社会应该怎么办、家庭应该怎么办、学校应该怎么办、对孩子的要求应该怎么办的一套方法。现在的社会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横的竖的都联系在一起了,要解决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只用一种方法,而是要有综合治理,就是说不是一个部门、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单位、不是一种方法,要一起来想办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统计之都: 刚才说统计是各个学科的一个工具。但我觉得如果一直在一个比较集中的培养环境,可能是一个劣势,比如刚入学的同学对统计学的概念常局限在比如应用经济等领域,大家可能在天文、心理等领域等了解就很少,大家如果想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途径可能就比较有限。如何才能拥抱星辰大海?
袁卫: 这个问题不仅仅我们这儿有,我曾经讲过哈佛大学孟晓犁当年的故事。孟晓犁从 2004 年起担哈佛大学统计系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统计系的规模急剧扩大,几年时间,本科专业的学生人数从个位数增长到 70 多人,而统计系的核心本科课程也越来越受欢迎。在统计分析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的时代,以及从遗传学到天文学等领域的突破要求更复杂数据处理技术的时代,孟晓犁一直致力于统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应用,他组织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参与生物学、医学、化学、工程、经济和卫生政策——甚至历史和语言——的研究项目,并将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和课程中去,现在,统计学已经成为哈佛最受学生欢迎喜爱的学科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 2012 年是大数据时代的元年,统计也伴随着大数据时代越来越火。美国统计方法的应用十分广泛,而我们的统计应用主要盯着宏观经济数据,自然科学的各领域,社会、心理、教育、历史、语言、考古,以及政治、法律的应用很少。我们的老师还没有进入各个领域应用、寻求合作,当然就缺少生动的案例,大家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宏观经济或是金融领域,研究的问题也比较雷同。
统计之都: 对于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导师制,能不能请统计学院和经济学院或其他学院的老师共同指导,是否有可能实现?如果要实现可能有什么难度?
袁卫: 绝对有难度,但是可以实现。如果研究某一个问题,它可能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你会有一个主要的导师,一旦研究深入就可能用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就需要深入到其他学科领域。过去同学从大学入学,一直呆在一个学院。现在,我们开始大类培养,比如人民大学的理科专业开始都在明理书院,同学接触的知识和领域更宽。但学院之间的沟通和交叉融合还不够,同学们自己应该更多地交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朋友。
统计之都: 在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企业会有大量的自有数据,同时也有大量的资金。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会发现好像在很多应用领域上,企业走在了学校前面。您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袁卫: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企业是真正的市场驱动,他们要做出有用的东西,市场有非常强大的需求,他们就会投入。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或应用型的技术走在了前面,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很多应用的东西,你让一个学校规划好、设计好,这很难。一个大项目,从研究到立项、从立项到招标竞争,不管是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是地方资金立项都需要时间,很快,一两年就过去了。但市场发展非常快,企业有这个需求,也有资金,很快就把人、财、物配置上来了,立刻就可以组织团队,开展研究。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研发投入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是反映研发投入大小的指标。各国通常用 R&D 占 GDP 比重的大小来作比较。我们国家教育的财政投入目标要占到 GDP 的 4% 以上,R&D 投入达到 2% 以上,2020 年我国 R&D 已达 2.4%。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占比更高,美国约在 3% 左右,日本约在 3.2% 左右。在研发投入中,企业研发的投入要大于政府的投入,越是创新的企业,研发投入越多。我们都知道华为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这与他们研发投入力度大有直接关系。2020 年华为营业收入 8913 亿元,研发投入 1419 亿元,约占 16%。我国 2020 年企业的研发支出约占全部研发支出的 3/4,因而企业在应用方面走在前面是很自然的。
统计之都: 刚才说到研究这一块,很多好的作品都发国外的期刊,然后,关于国内的期刊,您觉得是不是需要增设一下?
袁卫: 我觉得统计办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非常难。现在的四大(JASA、AOS、JRSSB、BKA)都是有很长的历史积淀,像 Biometrika 1901 年由 K·Pearson、F. Galton 和 W.F.R. Weldon 3 人创办,美国的 Annals 也很早,实际上 1931 年先是有一个 Annal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1973 年改成 Annal of Statistics 和 Annals of Probability。因而,一个好的杂志都是有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当然现在的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比如机器学习,自然就会有新的杂志,但是一个好的杂志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的。说到杂志,我们学院参与了 “数据科学” 杂志(Journal of Data Science)的创办。这个刊物在新世纪初的 2002 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研究所原所长赵民德先生主编,我们人大统计是 3 个创办单位之一,我是 3 位执行编辑之一,现在我们学院把主办权接过来了。
图 9:Journal of Data Science 的创刊号,2003 年
这个杂志创办差不多 20 年了,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英文杂志,但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够。这个杂志从开始办刊就完全按照国际高水平杂志组稿、审稿,我们编委会的人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发表在上面,就是希望它是纯国际性的,纯靠文章的质量来吸引读者。杂志与作者是联系起来的,好的杂志吸引人,杂志的声誉高才能够吸引一些水平很高的文章。国内也是一样,也有很多新办的杂志,但一个杂志需要编委或主编长期致力于提升它的质量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内统计学的刊物已经有几份了,关键是质量和影响力。
统计学的未来
统计之都: 刚才谈到许多现状问题,我们下面畅想一下。在您的梦想中,30 年后世界最好的统计系或者是统计体系生态是什么样子,或者与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袁卫: 这个题目太难了。这让我想起 1994 年美国加州伯克利统计学系的毕业典礼上,Breiman 教授畅想了 25 年后的统计学系。他对统计学和数据科学的未来做了漂亮的描述。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觉得未来,不一定 30 年,一定是一个数据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我相信每个学科,特别是与数据相关的学科,会越来越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那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学科的分界,授予的学位不再是现在的十二、三种。那个时候孩子越来越聪明了,各种训练越来越多,周边的环境越来越便捷友好,我希望那个时候孩子有更多的兴趣去探索未知,而不是更多涌向利益。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时代。
就统计学科来讲,我相信不用说 30 年,也许 10 年之后,数据科学的和别的学科交叉融合,一定是个必然的趋势。
昨天我和一个搞统计史的老师聊天,谈到我们能不能在统计之都上有一个栏目讲统计史,兼顾国内外,以一些风趣、实用、有启发的故事为主。
统计之都: 非常期待!我们一直想通过科普统计史来宣传统计学思想,让各行各业、各个学科的人去了解统计历史,从而启迪未来。
袁卫: 为什么学科史重要,学科史其实是很花时间、很花精力、不容易出成果的,成果也很难认定。我现在不需要评职称,也不用考核,完全是凭兴趣。我们的党史、共和国史、学科史都十分重要,我们老说历史是个镜子,这话老这么讲,我越来越切身体会到。什么叫镜子?镜子就是照自己,你看看你自己,当然镜子也有更深远的景象,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镜子,从历史看未来。镜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警戒” 自己。你们可能看过很多名人的年谱,编年形式的、记载一生。我们的学者一定要非常地珍惜和爱护自己的声誉,对每一篇发表的文章都要极其慎重,因为一旦印成了文字,不管这篇文章是 A 类、还是 B 类、还是 C 类,就永远被记录下来了,永远抹不掉了。你随便写的文字、谈的观点,自己可能都忘掉了,但文字永久地留在那里,也许就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大数据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删除”。
统计之都: 期待您的系列文章在统计之都发表。
袁卫: 不仅仅我,我可以组织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平台给有兴趣的人交流和传播。
学生培养、就业和建议
统计之都: 非常期待!关于在校学生的学习,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内卷现象?一部分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追求了,选择躺平;也有一部分人就只是追求能光鲜简历的那些条目。
袁卫: 你们提到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教你们《统计学概论》这门课,到今年一共教了 11 年,这期间每年的学生差别不大。将 10 年前后做个比较,我觉得本科新生的智力和知识的准备方面,数学基础、计算机基础无疑是越来越强,也就是说智商方面,比过去有了提高。但我同时感到,情商方面,就是人的品德素质、道德、基本的学习动力等方面,似乎不如 10 年、20 年前的本科新生。现在 18 岁左右的新生,学习的主要动力似乎不是兴趣和对知识与能力的追求,而是分数、学分绩、保研、将来的工作以及工资收入等利益的衡量。原因在哪儿?主要是社会的问题,物质利益似乎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追求,这影响到家庭、影响到中学,自然影响到每一名大学生,这个问题值得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思考。
图 10:袁卫给本科生上 “统计学概论” 课
统计之都: 一些跟数据科学相关领域的毕业生,更多去金融或者互联网行业,而一些传统行业,比如生化环材行业,则去的人比较少,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袁卫: 道理非常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利益驱动。最典型的例子,前几年全国的高考状元,基本都到了北大清华,几乎 80%、90% 都去了北大光华和清华经管。这些孩子里边一定有对天文感兴趣的同学,有对物理感兴趣的同学,……,但为什么都去了光华和经管,就是因为学金融赚钱多,这不是真正的兴趣驱动,而是利益在驱动。就是这么简单的例子,我们作为老师看着这些孩子还是挺担心的,当然我们怪不到同学,而是社会出了问题。
统计之都: 您对在校生有什么建议?
袁卫: 我在上课时说过,本科 18 岁到 22 岁左右,研究生再多几年,这段时间是人生中非常珍贵且美好的年龄。不能说分分秒秒,但是我觉得至少每一天、每一周都是十分珍贵的。对在校生来讲,很多同学们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觉得我考入大学就达到了目标,可以放飞自我了。但我觉得在享受青春年华的同时,要意识到我们的这一段青春对于一生来讲的价值,就是要做一点对一生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不论是学习知识、提高能力,还有强壮身体,以及磨练我们的精神情操。我总觉得现在同学们的智商我不担心,他们在智商训练培养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我真的希望同学们要注意品德修养,也就是素质,包括待人处事、谦虚谨慎、团队精神、毅力磨练等。
统计之都: 我们知道您很擅长摄影,可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吗?
袁卫: 我觉得人总是要有点兴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爱好,摄影是我的爱好,但是我不参加任何的摄影比赛,他们老说袁老师你去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我从来不参加,因为照相对我只是爱好,我拒绝任何带商业性质的事情。说起来,我从 1967 年就开始接触彩色照相了,应该说我是中国最早玩彩色摄影的业余爱好者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外汇有限,从国外买来彩色负片主要是拍一些新闻纪录片。大家知道黑白和彩色胶片是有保质期的,尽管将胶卷放到暗盒里边,但它不能够长期存放。存放时间超过两三年,胶片感光度受到影响,色彩也不能完全还原。在没有数码技术前,都是先用胶卷(负片)照相,冲洗后再印到相纸上,黑白如此,彩色就更复杂一些。黑白照片洗印放大时,暗房中有一个红色的安全灯,可以在红光下操作。但彩色胶片和相纸对各种颜色都感光,就需要自制单独的特殊的安全灯。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几个电影制片厂不再拍故事片了,当时从东德和西德购买的彩色胶卷开始过期。1967 年初在前门大栅栏红光照相馆开始廉价处理过期的彩色胶片、彩色洗印药物和彩色相纸。我和我二哥是第一批玩彩色的业余爱好者。
图 11:1969 年 9 月 30 日,新中国 20 岁生日前一天的天安门广场(袁卫拍摄,彩色负片洗印放大)
1969 年我们国家二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我已经到兵团去了,还专门回京去拍天安门,也拍了夜景,应该说是很宝贵的照片。我去兵团的时候,把没用完的彩色材料也带过去了,自个儿周末或者有点时间也会拍,一直延续到后来。后来就忙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不过出差的时候有空去拍点,也就是这样。我办公室那些放大的照片都是我出差或出国抽空照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多少有点儿兴趣。像我们老了就多了一点生活情趣,姑且不说摄影知识和技巧什么的,至少通过照相可以交朋友,外出背些器材锻炼身体,还是挺好的。
统计之都: 您对统计之都有什么建议和寄语?
袁卫: 从一开始谢益辉创办统计之都,一直到你们接棒,我觉得办的还是挺好的,已经成为学习普及统计知识,提高兴趣的平台。随着我们统计学科的影响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还可以动动脑筋,做得更好,预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敬告各位友媒,如需转载,请与统计之都小编联系(直接留言或发至邮箱:[email protected]),获准转载的请在显著位置注明作者和出处(转载自:统计之都),并在文章结尾处附上统计之都微信二维码。
Recomm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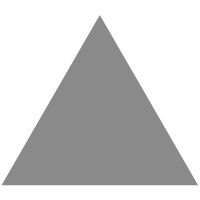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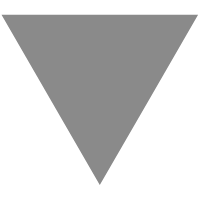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32 期:合肥 R 会议主席—林枫 关键词:COS 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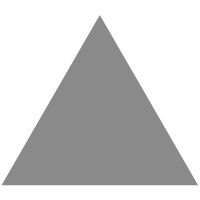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3
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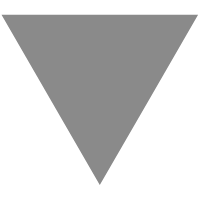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24 期:郭绍俊老师 郭绍俊 / 冯璟烁 / 于嘉傲 审稿:于嘉傲;编辑:冯璟烁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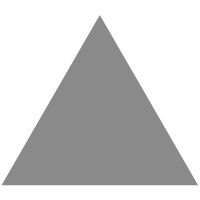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5
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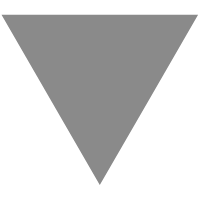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25 期:李东老师 李东 / 张心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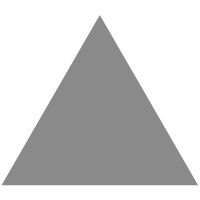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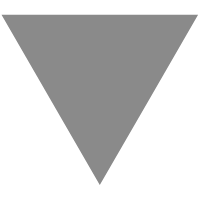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33 期:刘三震老师 刘三震 / 谢益辉 关键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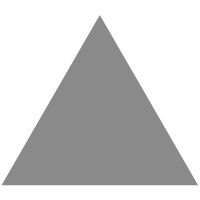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3
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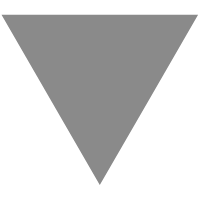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30 期:宗福季老师 关键词:cos 访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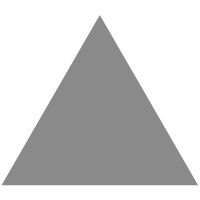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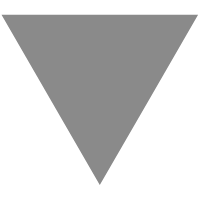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31 期:Charles Stein Morris H. DeGroot / 王佳 / 张晔 关键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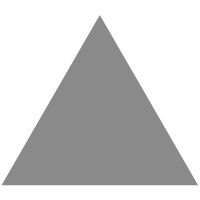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5
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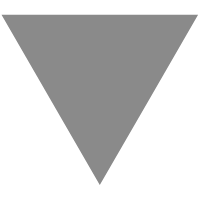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第 19 期:张志华教授【COS 编辑部按】 受访者:张志华 采访者:常象宇 文字整理:王莉晶 朱雪宁 张志华,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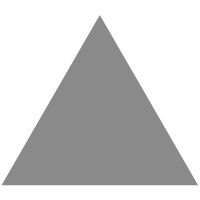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5
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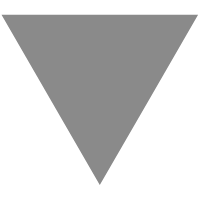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3 期:易丹辉教授 易丹辉 / 陈堰平 关键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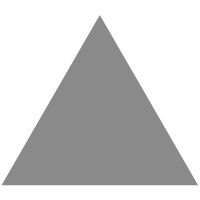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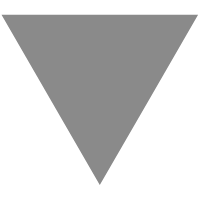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11 期:郁彬教授 郁彬 / 施涛 关键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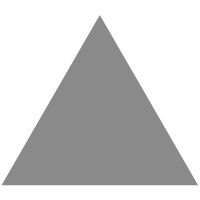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3
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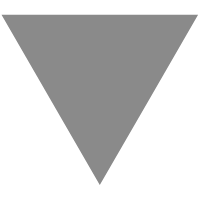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COS 访谈 COS 访谈第 41 期:统计大师 Donald B. Rubin 教授 关键词:cos...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