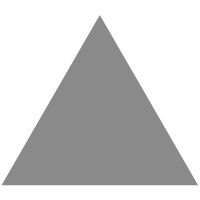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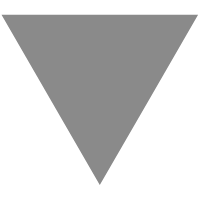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用文字打败时间 » 2012 » 10月
source link: http://www.fengtang.com/blog/?m=201210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2012-10-9 05:56 下午
关于文学:和格非问答(转自《时尚先生》2012年9月刊)
冯唐:你为什么写作?
格非: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比较寂寞,也不会和人打交道,自己还比较拧。想赢得尊重,但没有任何实力,别人怎么尊重你?很多场合就会受到冷落,遭遇多次之后,就会有愤怒在心里发酵,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写作是一种释放。
冯唐:成名之后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格非:1994 年后的一段时间,就没动力了。有个时代的气氛在那儿,90 年代文学完全市场化以后,作家普遍都很担忧。我们在海南开过一个会,大家讨论的唯一问题就是作家们以后会不会被判死刑,作家们在商业化以后会不会饿死。从1994 年到2003 年,我什么都不写。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写,自己就不要再丢人现眼,算了吧。后来重新写也有很多原因。经过十年的思考,终于想清楚了一些问题。读了很多的古书,没有白读。比如黄宗羲问过,国家都灭亡了,你还要做学问干什么?他的回答是,虽然国家亡了,但是三百年以后还会有圣人出现,他还要提供自己的智慧,可以等待后来的人发掘。这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写作,给出的一个答案。我也一样,不需要在乎一些东西—名声有多大,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都没有关系,假如提供了一流文本,对未来的影响谁都不能抹杀。
冯唐:很多作家都面临过一个问题,创作停滞了一段就很难再写,或者写的水准和以前有一定距离。你十年没写,怎么恢复的状态?
格非: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冯唐:对写作技艺提高的追求,会成为继续写作的动力么?
格非:会。说句老实话,我在看博拉尼奥(智利作家)的《2666》之前,还是有一点狂妄的。但是我看一章,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发现,自己跟他差距还是蛮大的。这让我有点吃惊。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会热血沸腾,会被煽动起写作的欲望。
冯唐:你在大学里教写作,你觉得写作是可以教的吗?
格非:小说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冯唐:可以定义一下,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格非:要丰富,方法上最好能够简洁,在基本生存上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超越到哪去呢?可能是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比如说接近上帝。另外像日本的小泉八云,他的作品读完了之后,能让我们心里产生某种向善的要求。或者,有助于去了解我们欲望的秘密。欲望在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还在控制我们,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够带我来穿透这些。
冯唐:你、余华等人都曾被人称为是先锋小说家,在结构、写作上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什么近年这些尝试反而少了?
格非:那是年轻时的状态。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冯唐:这是做了结构性探索之后的回归吗?
格非:不能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跟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写作,刚好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形成了巨大影响。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重新看其他类的作品,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是白痴。这可能跟人的年龄,经验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和时代有关系。今天的80 后、90 后他们刚开始接触的作品就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是从日本的、韩国的开始的,比如村上春树这种类型的。也许他们最终能走出这个影响,也许走不出来。当年我们要走不出来,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家,在当年做过一些探索,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此而已。
冯唐:你跟同辈的作家聚的时间多吗,频率高吗?还谈文学吗?
格非:很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些哥们原来在80 年代的时候见一面,除了文学什么都不谈。现在是相反,见了面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谈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当然你要谈,别人也可以跟你谈,但是大家都不谈,彼此都心怀鬼胎一样,大家都不触及这个话题。
冯唐:现在你教书、做研究、阅读和创作,关系怎么摆法?
格非: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然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书,其实我事后想想,背后是有种逻辑的。比如说你苦闷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快乐的书,肯定会去找也许能帮助你的书。我有段时间很苦闷,有一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保罗•蒂里希的《生存的勇气》。研究跟教学这方面这是本职工作,也就是必须做的。
冯唐:为什么苦闷?
格非:精神上的危机,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人到了35 岁左右可能都会有,我比较严重,大概持续了四五年。
冯唐:35 岁之后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么?
格非: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总会对某些事特别恐惧,对某些事情又特别渴望,很容易把某种东西神圣化,把想要的东西极端化。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到了三十多岁,突然发现世界上没有太多东西让你恐惧,也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好得让你一定非要得到它不可。那时,会对人的艰辛,对世界上的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会对人的不自由、受到的限制有更深的体会,会体会得到更多无奈。人也会变得更宽更厚。对人的看法也会发生根本的逆转。我在年轻时特别讨厌罗嗦的人、不读书的人、肤浅的人,可是中年以后就变了。我发现其实人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很多有学问的人其实很虚伪,很多很笨的人,没怎么读书的,其实天性当中倒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有一些人他确实很庸俗,但至少他很真实,比那些虚伪的人不知道好多少,所以慢慢看人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对人性的理解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交往的对象也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只跟有名的人接触,后来我跟什么人能交朋友,都能聊天。
冯唐:你怎么看个人声望?当年马原很羡慕你,说你30 岁就已经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在《收获》 上。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格非:我记得,我没觉得那有什么。我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当然我对写小说还是野心比较大,但对于出名什么的没有太大野心。名声这个东西,它会给人造成错觉,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人类有时想想很悲哀,人会对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着迷,然后你会受制于它。艾略特曾经讲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这个话我们很早就知道。
冯唐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就选一位。
格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无数在我看来不能克服的障碍,这个太难得了。他个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同时也面临时代大转折。这两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时代有两个巨大的变革,整个社会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宗教支撑的西方理性主义世界都在垮塌。需要最敏感的人,最优秀的人来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回答,我们怎么办?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通过爱,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卑微来获得我们所要东西,而不是说像尼采说的那样,通过强力、强人重新建立秩序。 这个方面他带有宗教的光芒。他的这种方法我更认同。
冯唐:你信仰宗教吗?
格非:我不信仰。
冯唐:那你觉得人应该有宗教情绪吗?
格非: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感。没有宗教感那就只有利益了,能够超越利益的就是宗教感,没有这个会很危险。我不太愿意信教,因为信教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制度本身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冯唐:你怎么看当下的阅读气氛?
格非:这有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不爱阅读了,主要是价值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不太关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我们会把自由看成有没有钱,追求的无非就是一有休闲时间去旅游,我去新马泰、去欧洲,你只能到周边。我用苹果4S,你用什么。我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大家就比这个东西。物质化已经把人带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物质化所导致的污染、导致的过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时代,你说整个阅读的氛围会好吗?我想大家都会被那种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被偶像迷惑。创作者也会发出怪腔怪调希望来蛊惑对方视线。大家都这么做,可想而知这个文化会发展到什么地方去。我把现在的文化看成是一个偶像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我觉得有质量的阅读会非常少,但一定会有。我一点都不悲观。有了互联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的微博,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在读一些只有专家们才会读的经典,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然这些人说老实话有点烧包,有点虚荣心,或者说有一点显摆,但那也挺好。
冯唐:你现在读什么书?
格非:我看的书很杂,我最近在看中东史。我突然发现知识储备里有个最大的盲点—波斯。去年我看了奥马•哈亚姆的《鲁拜集》,吓一跳。11 世纪在波斯居然就出现了那样的诗歌,真了不起。劝人及时行乐,既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魔鬼又是天使,天国就在你的心中。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言论,但在11 世纪已经出现了。我看书是这样,突然对哪个地方我感兴趣,我可能会集中找一些书来了解一下。也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对我创作有没有用。
冯唐:你怎么看当下的写作气氛,热爱写作的年轻人,跟你年轻时一样多么?
格非:不需要很多。很多人看待整个的文学版图,会考虑有多少人写书,多少人坚持。这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一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好作家。当然19 世纪后期是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你看看中国清代之前,有时一两年出一个作家,有时两三百年才出一个,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我觉得不需要像工厂一样批量生产,当然也生产不出来。
冯唐:那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格非: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既不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阴暗的时代。它不是人类处在上升期的充满着朝气的那个时代,不是。它当然也不是黑暗的法西斯的那种时代。它是一个阴暗的,有各种可能、各种危险、各种无奈纠缠在一起,相对复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事情你看不清楚。这个时代给作家、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更严峻,今天一个好的作家,他不仅要有智慧,他还需要有历史感,才能面对这个时代的诡异。
冯唐:历史和时代给你很大的影响么?
格非:当然是。历史分成几个部分,一种是特别古老的,连你父亲都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历史是你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文革之前,50 年代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能够猜出来,但是辛亥革命你可能就推测不了,它离得太远了。历史事件距离远近对人造成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讲,越是离你近的事情,你越容易把握。但是写小说是相反的。近的反而难以把握。正因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也纠缠在事件当中,比如改革开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冯唐:你怎样选择写作的题材,这些会不会进入您的作品?
格非:当然会啊。但我进入的时候,可能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写小说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最笨的方法。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去查资料每年发生什么事,然后塑造几个典型人物,用这些人物代表这个时代。这是最烂的,最不好的写法。第二个写法呢,把这三十年的经历变成情感,把握这种情感,就会变得真实的多。你真的要概括这个时代很危险。但如果把情感把握住了,就会大致准确。这是第二种写法。我觉得最难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是第三种,就是去写人的精神状态。后两种方法我都会用,反正我不会采用第一种。
冯唐:你认为60 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有没有共性,有什么样的共性?
格非:跟50 年代出生的人是有点不同,到今天他们那代人对我们来讲,都还有神秘感。他们思考问题更深邃,不是哲学上那种深邃,而是说他事情还没做,已经考虑到事情的结果,预料相对准确,有很好的嗅觉,很多人也特别会玩阴谋。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分寸感,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进都很清楚。60 年代的人没有这些东西。60 年代人也油滑,虚伪,但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我也不是说他们中没有好的。)70 年代的人,这点上还算跟我们比较接近,但80 年代的这些孩子已经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我上课,他们经常跟我我说,老师你痛苦什么啊,关你什么事啊。再有60 年代的人是一个全息式的,就是说他什么都能做,你要把他一个人扔到欧洲去,他们也能很好生存会做饭,可以精打细算,所有事情都难不倒,这是在艰苦环境里磨出来的。
冯唐:20 年前你们就在讨论,你们那代作家肩负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反而现在很少听到了。
格非:老实说,作家提供的是个备选的东西,作家从来没有说他要去改变时代、改变世界,他也不可能。卡夫卡改变世界了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一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发表在网络上也好,媒体上也好,或者出版。大家去不去看你的作品,大家对你还需不需要,对你的价值是否有充分认识,有时不是作家的才华能决定的,要根据时代各种因素的变化。没有两次大战,卡夫卡是不会出名的。对于国家机器产生的那种荒谬,对于人失去故乡这种特别纠结的情绪,对于物化、异化,卡夫卡形象地说明了,我们觉得他非常伟大,假如说他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就很难说了。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不朽与否千万不要去想很多。这个不是你的事,你想也没有用。我们今天的作家,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喜欢各种奖、名声,在批评家笔下的地位怎么样。这在我看来是很可笑,你用人力去干预一个本来根本干预不了的事情。你死后影响再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
冯唐:你很年轻的时候有过要改变中国的想法吗?
格非:现在也有,但是我一直告诫自己,有些事情是我能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
冯唐:什么是能做的?
格非:我觉得中国需要全方面的改变。这不是说政府换了,出现了什么人物,这个国家就变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做事。比如说很多做NGO 的人会跟我说,你们这些研究思想史的、写小说的人,这些领域根本没用,还不如我们这些人到农村去帮他们搞医疗,帮他们去建立医疗系统,去发展乡村教育。当然这些具体工作都很重要。但是重大历史变化全部是思想促成的。我并不觉得我从事的和社会没关系。当然我写的是小说,可能跟纯粹的做思想史不太一样,但比较相似。陈寅恪说过一番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上个世纪50 年代,因为体制的变化,他的弟子蒋天枢对前途绝望,给他写信。陈寅恪回信讲了欧阳修修史的典故。五代时期,中国经历了几百年巨大的混乱。宋朝开国以后,曾有人写过一部五代史,欧阳修觉得写得不好。他希望能正一代风气,使乱臣贼子惧,于是自己重写五代史。陈寅恪说,一个人通过一己之力就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使腐败的风气变得淳正。你现在教书,怎么说自己没有作用。陈寅恪这个话说得很厉害,也激励了我。
上一篇:不器:随身佛(GQ中文简体字版专栏2012年10月)
下一篇:不器:机械手表(GQ中文简体字版专栏2012年11月)
2012-10-6 10:09 下午
不器:随身佛(GQ中文简体字版专栏2012年10月)
我们这一代的正规教育里没有宗教。
没有宗教的教育强调的是如下内容: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石头变的,石头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爆炸之后形成的;人定胜天,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个体是渺小的,组织是强大的,领袖是正确的,任何内心的软弱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糟,资本主义糟,社会主义好,封建主义已死,资本主义必亡。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大,那时候,没有宗教,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小孩在天地间疯跑,不知道名利为何物,学习基本常识,食蔬食饮水,应付无聊的课程,傻愣愣地杀无聊的时间,骂所有看不上的人“傻屄”。本身近佛,不需要佛。
第一次的宗教感来自一个高中时代的下午。秋光脆亮,秋云不动。我在水泥案子上打乒乓球,对手正手攻球打飞了,我转身跑去捡球。我拾起球站起来的一瞬间,仰头看到不远处一个练长跑的女生背对着我,双手紧握双杠的一根,压肩膀,我不认识她。
她的肩压得很低,黑直头发梳成马尾,随重力垂下,最低处低于她臀部的最高点。她的小腿腓肠肌拉得很长,挣脱运动裤,近脚踝处裸露出一段,和裸露的脖颈呼应,对抗重力向上,似乎一直延伸到臀部的最高点。太阳被云遮住一部分,遮不住的光金子般从云彩边缘倾斜而下,一阵风从无何有处升起,操场上的国旗、白杨树的叶子和那个女生的辫子朝一个方向飘扬。那一瞬间,我完全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深深感到,她是高级太多的物种,创造她的不是她爸妈而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如果没有外星人,那么或许有神。
下一个瞬间,我的乒乓球对手在水泥球台的对面遥远地高喊:“快打球啊,马上要上课啦,发什么呆啊,你丫傻屄啊。”
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不成系统地阅读佛经,特别是禅宗文字。一是为了增加些佛教基本常识。在国内到处走,到处都是历朝历代甚至当代的寺庙,寺庙里面那些花花草草、神神鬼鬼都是什么啊,我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二是为了大处着眼,拿佛的形而上做个救生圈,让我不要陷入名利的大海里不见天日。不时翻两页佛经,扯脱一下,套着救生圈,上半身浮出水面。三是为了消化禅僧们在汉语上的实验成果。在探索汉语甚至语言的可能性上,某些唐宋禅僧走得比唐宋诗人和词人更远、更荒芜。
佛经里常常有插图,画里的佛常常健美得仿佛长跑运动员,尽管都是正面像,但是我知道,她们的背面都有着漫长和坚实的腓肠肌。
我有个朋友专营佛像,石头的居多,也有铜、木、铜鎏金的,绝少玉的,仿的居多,也有真的,锁在保险柜里,不摆在外面。他的生意在春节前和“两会”后特别好,他说,“越是心虚的人,买的佛越大。”他的店是个小套间,里面一间有个沙发,沙发下面有个塑料盆,塑料盆里常年一盆酸水,酸水里横七竖八泡着好几个佛。我说,你也太实在了吧?孙二娘也是不小心才把人手指骨头包进包子里,你做旧的酸味儿在楼道里都闻得见。他嘿嘿笑,还是继续泡。
他知道我收集高古玉器为主,很少碰佛像,但是总想卖我点佛像。我说我到处跑,平均一周跑三个城市,拉杆箱是真正的家,如果买个仿造铜佛,占半拉箱子,其他东西怎么放?过关被海关拦住,他们如果分不出是仿造,我怎么办?他打开保险箱,说,可以买随身佛啊。
我先后在他那里买了五樽随身佛,三个铜鎏金,他说了三个佛的名字,我都没记住,两个粘土烧的随身佛,他说了另外两个佛的名字,我也没记住。他说这类粘土烧的随身佛叫“擦擦”,软泥按入模具,烧制而成,和做饼干、月饼类似,讲究的烧制后上颜色,甚至有的“擦擦”后面有高僧的指印。
其中一个“擦擦”常住在我的拉杆箱里。我很少求它办什么具体的事儿,比如这班CA981不要晚点啊、这次五个小时的高速路不要出车祸啊、某个股权交易一定要完成啊之类。晚上,我把它从拉杆箱里拿出来,摆在酒店的床头,恭敬地拜一下,拜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想法,仿佛早上出门和太阳点一下头。
只要知道这个随身佛在附近,和那些所有美好的未知一起真实地存在着,我就会心安一点。有次,我和我妈说,如果我死在她前面,我的肉身烧成灰儿之后,建议她把灰儿拌了粘土,烧几个“擦擦”,随身带着,百毒不侵。我妈说:“你妈。”
上一篇:不器:纸书(GQ中文简体字版专栏2012年9月)
下一篇:关于文学:和格非问答(转自《时尚先生》2012年9月刊)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