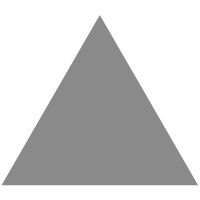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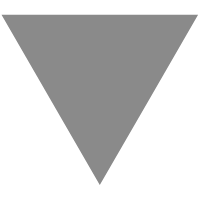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我在五台山做义工
source link: https://sspai.com/post/88078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我在五台山做义工 - 少数派

Matrix 首页推荐
Matrix 是少数派的写作社区,我们主张分享真实的产品体验,有实用价值的经验与思考。我们会不定期挑选 Matrix 最优质的文章,展示来自用户的最真实的体验和观点。
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少数派仅对标题和排版略作修改。
去年夏天,已经家里蹲了将近三年的我决定多多少少要尝试将自己的人生往外推一点。充裕的时间、较为紧张的经济条件、希望尽可能远离家庭与城市的意愿、对于佛教的信仰,让我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之前旅游过且充满好感的五台山。那是世界佛教圣地之一,相传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中有寺庙大大小小上百座。又处于山西太行山脉,我是福建人,这是一段足够远的距离。而寺院素来有招收义工干活的传统,一般要求不高,管吃管住,我想那里必然会有我一个短暂的容身之处。
不知道有多少人将寺院视为逃避的场所,认为既然也不是出家,loser 才来到这样「清心寡欲」的地方每天啥也不干就念经吃斋。实际上,要维持一个机构每日的运转,有很多大小活计需要承担,很多寺院人手不足,常年需要义工。我的所有工作履历已经断档三年,在社会定义里,我应该就是一个 loser 了,但是寺院却是我在生命的阶段里,鼓起勇气准备往前迈出一步时,一个让人感到安心的、可以接收我的地方。
尽管如此,出发之前我还是焦虑到失眠了,害怕去远方,害怕呆那么久会发生什么,害怕找不到寺院要我我又只能很快回家,害怕自己这么久没有工作是否已经和世界严重脱节……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不安在到达五台山那天达到顶峰,因为我和原定计划要去的寺院联系,得知他们的义工人数已经饱和不再招新,一下丧失了控制感,顿时紧张了起来。只能和同行的朋友先做起游客,打算在其他寺院逛逛问问。
第二天坐景区小巴环了一圈五台山的五个台顶,即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头,海拔也由景区镇中心的 1500 米攀至 3000 米,这个路程坐车都需要九个小时才能环完,也称「大朝台」。

7 月份,镇上还是炎夏,而那天的台顶注定要下雨起雾。气温降得很低,每辆小巴车载着瑟瑟发抖的乘客们在蒙蒙细雨和视线极差的小土路上颠簸前行,路上经过寺院司机就会把车停下,乘客们下车进入朝拜或观光。那一天的景象,在我这个初见华北广阔山境的人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震撼,时至今日那些画面,都能在这个忆起的当下使我得到短暂的停歇。




正如我所说的,那天注定要是一个下雨起雾的日子。中途行至某寺院时,我同样下车朝拜,却在一个转角,天女们仿佛等待了我许久般地降临。那天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游客稀少,我有足够的空间,在这些塑像面前独处,无法挪动脚步。心里感觉到,就是这里了。



回过头,我看到有位穿着围裙的大姨正在扫地,我向她询问义工一事,大姨高兴地回答:「招的呀!来吧!」我也很高兴,仿佛定心丸吃进嘴里了。

第二天,我拖着行李箱又坐上了景区巴士,不过这一次不跟着环线下山了。天气与前一天截然不同,晴朗的高海拔阳光直射洒遍每一个角落,朝台线上的停车点人头又熙熙攘攘起来,我直冲山门,找到大师父,开口就说:「师父!我想来做义工!」
师父仍然一边忙着手上的活,头也不抬,没有回应。我的心里才开始急起来,想起昨天也忘了问人家是否对义工有所要求,自我的念头往外蹦出,万一我不符合怎么办?是不是我的头发染太黄了?在传统寺院不合适?我不会又要下山去吧?……沉默持续了一分钟,师父才悠悠地抬起头来,指着远处的一栋建筑说:「去客堂等我吧。」
我的心又振奋了!

金莲花圃,背景就是客堂所在的长条形建筑

钟楼旁的煤堆

寺大门
在客堂登记信息后,我放好行李,这才有了尘埃落定的感觉。当时还没有给我派活,我在寺院里先转了一圈,轻松又兴奋,第一件事是去看看晴天的妙音天女们。


寺里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很多,甚至还有三分之一是前一天因起雾看不见而被我忽略过去的面积,那是一座标志性的大白塔。山上的寺与寺之间又相隔好几公里,随手一开窗、一推门都是望不到头的旷野。浩瀚的世界自此延展、身心自然。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觉得天女塑像真美以外,我什么都没考虑就来了,我是有多么幸运。大师父是个比较看缘分的人,也不是啥人来干活都要的。再来,我所在的寺院算是山上的寺院中条件很好的了,通自来水、电,义工有洗澡的浴室,储藏室里的菜、面、油满满。其他有些寺院吃饱都成问题,也不通水,师父们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这也都让我对以前城市里唾手可得、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产生一点如梦惊醒之感。
这天,我坐在一出后厨即是远山的围栏上,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想到就在这住下了,做梦都会笑醒。

这就是从后厨出来,一推门的风景


至此,五台山已经给我上了两课了,我那些微小的焦虑恐惧都浮上水面、被照亮了;以及,对恩典的感受。我发现我已经开始不再去想怀揣着的那些疑惑,当你不再需要一个答案时,问题本身也就消失。
这就是答案。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家超过半个月的时间,我想在很多程度上我肯定是一个被惯坏了的独生女,但我适应和融入得比想象中都要快和丝滑。
我们寺里规矩不多,通常义工们之间不论男女老幼都是互称「师兄」的,但有时我感觉这个称呼有点说不出口,经常姨啊哥地叫大家。我被分配到山门干活,我的「领导」,一位吉林大爷,姓赵,已在寺里护持二十多年了,大家喊他赵本山,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憋急了喊我「小娃娃」。当时寺里东北人多,除我以外最南的南方人就是河南人,几天以后我的口音就歪了,有一股闽南大碴子味,大师父为此质疑了我好几次到底是哪里人。天王殿的师父有时朝山门招手,想摇人过去干活,一看是我跑去了,挠挠头给我一袋红枣,再带我到文殊殿,从供桌后面掏出一颗大西瓜,让我捧回山门分着吃了。
山上气温寒冷极易大雪封山,每年景区巴士通车时间只有夏季几个月,又赶上暑假,几乎天天游人如织,许多人对山上山下温差之大没有预期,到了我们寺这里冷得发抖。同时五台山朝台路线不仅对于佛教徒来说是积聚福德的旅程,因为景色优美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徒步路线,步行过来的人里有磕长头朝山的信众,也有徒步爱好者,这些人走着走着也需要休息。大师父于是广开山门,每日我们把熬的白粥一桶一桶地送过来,供日均几千人流量的游客免费吃喝、暖身歇脚。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卫生、清洁地面桌面和桶盆、更新粥桶和菜盆、补充碗筷、人太挤时维持秩序、防小偷。


不过对于温差没有预期的同样也是我,五台山又称「清凉山」,七八月份山顶上和福建沿海的冬天一样冷,刮大风的时候如果不戴面罩,密度极高的风会结结实实堵住呼吸。如果你找对风口,打开一个水瓶往下倒水,水流只要一离开瓶口就被风吹走了,完全落不到地上甚至杯子里。只有一箱子夏装和从镇中心超市随便买的一件薄绒冲锋衣的我,在等待家人给我寄来衣服的那几天,天天在后厨跟义工大姨们嚷嚷好冷,姨们给我找来库里也不知哪些前人留下的服装,上衣是个大粉色,裤子腿根是磨破了皮白的,穿上姨们一直说好看,还给我拍了张照。


寺里年轻人不算多,干活的主力还是大哥大姐们,我在家里仅仅做做家务的那点力真是不够看的。山门配粥的咸菜由两位大姨负责,每日现拌,一做做上百斤,切菜、清洗、焯水、腌制一气呵成;后厨的常规配餐量是日均六十到三百人,三顿,有时赶上法会需要供品,还要更丰盛些;七十岁的老和尚每日用板车推换几大桶水,清理旱厕;大爷早起一锅一锅地熬几百斤的粥;我的山门师兄们,天天十几趟地穿梭于火房和山门之间,六十六升的粥桶抬二十几桶,一次一次地倾倒同人高的垃圾桶;司机大哥长途奔袭于山上山下,有时是突发急事的半夜;山上生态脆弱,寺里的金莲花是师父们一颗一颗栽下的,据说有几年了,还是挺稀疏的,有不明真相的游客企图踩进金莲花圃里,大爷怒发冲冠,一甩手把刚吃剩的西瓜皮叭一下丢过去,砸到此人脚边吓他一跳;最操劳的还是大师父,寺里大事小情都得找他。
我进来前还有点不知道哪来的「我能干活呀」的小普信,到了第二天已经不敢吱声了,弱弱地接受师兄们的嫌弃,比如,让我去火房烧火,这辈子就没起过柴的我把火弄灭了。


有一天晚上,和同屋大姨闲聊,我说我把咱寺写文章放网上会吸引好多人来做义工吗?姨很疼我,总是帮我带厨房发的吃的,但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是来的都是像你这样的,师父得气死……」
我哈哈大笑。
后厨还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妹妹,救过我三命。她圆圆的脸型,眼睛也是又圆又大,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比我小一岁却比我靠谱了十倍,在厨房能得到大姨们的一致赞扬——会干活。她也是那种当你自己一人提重物准备攒劲往上一努的时候,突然默默伸上来帮你抬住的那双手。话少,她好像总是在语言之前先观一遍心。
她救我的第一条命是有一天我冻得头掉,又在厨房门口嗷嗷喊,沉默的她主动开口借我一个她自己的毛线帽,原话还说,「就是有点脏,我老带着没洗,不介意昂。」接着递给我的却是一顶雪白的帽子。她又说,「注意保暖呀,山上的风可厉害着。」第二条命是有一天我单穿了毛裤,她碰到我冰冷的手,让我赶紧跟她上楼,又掏出一条超厚的秋裤,穿上我才有了一点重新做人的感觉。第三条命是某天我的垃圾食品瘾犯了,抓心挠肝的,而山上别说小卖部了,快递都要集中几天一起拉上来,好妹妹挠了挠头,过了一会拿着一瓶她自己背上来的健力宝出现了,仿佛一位手持甘露的仙女。
有一天日落时分,我在寺里散步,碰到好妹妹了,她说她去绕塔,我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走呢?她说,只要父母身体没出什么事就多呆呆呗。我心想,啊,是父母身体很不好吗?但又感觉这问题太隐私了,就没继续。然后她独自往着夕阳下远方的天穹去了。

此处即「文殊讲法台」,相传文殊菩萨在此演教说法。也是众多师兄常来绕塔修行的地方。


又过了一周,一天早上我刚踏进厨房准备吃早饭就得知好妹妹凌晨已经下山了的消息。姨说:她父亲半夜没了。我只能发出啊的一声,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帽子还没有还给她呢。我想说洗洗再还的。姨又说,她父亲年纪很大了。原来如此,我想。原来心里的问题也可以是这样子得到解答的。一朵云飘到你的天空中时好像很难被察觉,当它离去的时候,大家都会知晓。

我在寺里的另一项活是到钟楼打扫卫生。钟楼不对外开放,内有四层,大姨们会在清晨进去上香、做大拜,而我需要在下午进去将佛像抹一下灰尘,擦干净香灰,地一两周全楼拖一次,但位于三层的度母殿则需要每日拖地。女性形象总是更喜好干净的,我猜。
在高海拔提桶反复上下楼梯对身体还是有点挑战,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自己静静地呆在上下无人的钟楼里,静静地擦桌子,静静地拖地,静静地端盆换水,干完了静静地坐一会儿,脑子里嗡嗡地思考一些佛菩萨们在无人的地方是如何寂寂坐过每一天的,菩萨为什么可以在一个地方坐一年,坐十年,坐一千年。然后再一次吱地一声,打开度母殿的门,依旧从容不变的母亲们,环绕着唯一的我和我的抹布。



每天晚上大师父都会在一个房间内讲经开示,那些精进虔诚的师兄们节节不落,我则属于玩心过重的,第一天去听课时到处左看看右看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在灯房工作的师兄,四五十年纪的女性,几乎不和人说话,感觉她已经在这里很久很久了,因为我惊叹于她唱诵法本的熟练程度,偷偷看她快速变化结手印的手,每一条指纹里都是黑色的煤油——长时间清洗供灯的痕迹。






还有更多的教导在经堂之外,一天晚上,寺里一位老太太住客应是自己不慎丢失了一颗珠子,认定是两位阿姨偷的,她们恰好住在我隔壁屋,那时是本应熄灯了的九点多,老太爬上楼来站在隔壁房门口,声泪俱下作势要跪下,一会又口吐诅咒,两位阿姨尴尬地解释无济于事,这番动静最后引来了大师父,他也爬上楼来,手持念珠站定,老太以为当家的出来主持正义了,从头絮絮叨叨了一遍,大师父确实是来主持正义的——但,是更彻底的,超越生死二元的那种正义。他耐着性子听了个大概,在老太说到:「没有那珠子我就没命了……」这句话时突然出手,把手上的念珠串「啪」地一下打到老太的胳膊上,喝道:「没命就没命!谁不死啊?你还想活个千年万年的?!」
真是厉害。本来只是在旁边偷偷「吃瓜」的我,感觉这串念珠也突然一下打到了我心里,眼前明亮了一下,这大概是很多机缘下都无法深刻学习到的死亡教导。同时,和我一起吃瓜的室友姨乐得竖了个大拇指:「咱师父真是有魄力呀!这老太太八十了,换别人谁敢打她这一下。」




寺里的义工们经常来来去去,有人上山,有人下山,有人从此和你产生深刻的联系,也有人此生可能已经和他见完最后一面。我到寺里十来天后,当时同住的大姨们准备离开了,我在推测接下来可能会和谁住,紧接着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地方迎来送往时,会产生一种自己已经是本地人似地错觉。换句话说,更像家了。





每天下工以后我都会在寺里和周边散步,基本在下午五点过后,山头就会寂静下来。这里没有酒店饭店商店等商业的痕迹,旅游车载着大批人群下去了,只偶尔会有一些徒步者和住客在活动。山西天黑得晚,在晚上八点左右。寺院低矮的围墙外边即是大片高山草甸,经常,我结束工作后就去躺在草地上,接受大地的治疗。当我第一次躺在这里时,心中有一股柔软绵长的涌动,好像我人生的前三十年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不过实际上,这个体验并不是很安静,一般来说,能够躺下的天气不错的下午也意味着相对高的温度、比较小的风力,这使很多苍蝇会在你的头边嗡嗡作响。有一次躺着的时候,我给朋友打视频电话让她看风景,我说,有苍蝇实在太吵了。她说,苍蝇你都觉得吵那你下山回去怎么办啊?我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还会有蛇,地上有许多蛇洞,司机大哥说有时会看到蛇躺在路中央晒太阳,不过我没有遇到过。每天都会遇到放养的大片牛和大片马,牛的胆子很小,基本上有人近身一米内范围就跑了,马则好很多,马毛是粗短扎实的手感,马脸长,摸起来像手在滑滑梯。有好奇的小马宝宝还会跟在我屁股后面走路,啃我的衣服和相机。




躺在地上休息的小马,看起来也很像在耍赖

大姨们总是担心我靠马那么近会被它们后腿蹬,说一下子就可以踢断肋骨,不过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大概是我这个没怎么接触过放养动物的新手保护期吧。马牛多也意味着粪便多,虽然那也是草的养分,并且我躺在草地上看起来很美好,实际经常找不到一块稍微干净点的人形区域。有时闭着眼睛躺下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躺在一些陈年屎尿上,直到脑袋边飘来一股熟悉的味道。



喝奶小牛与牛妈

竟遇到了牦牛,唯一一次。看体型小,像家养牦牛

每天只要是在楼与楼之间穿梭时,就忍不住抬头看着天走,看着远方走。第一次从地面上看到清晰的阴晴分界、第一次知道乌云也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第一次见到「22 度幻日」这个天文现象、第一次见到远方的大雨如何在乌云层中落下、见到无数次雨过天晴,也在无数个日落时分,一抬头突然被一个遥远的成语击中,这个词是「霞光万丈」。在这样的夕阳下,没有人能忍得住一声又一声惊叹。






天气也有很不好的时候。首先,违背生物季节的冷是常态,在山上的四十七天暑季里,我只穿了两天短袖。虽说我一开始正是被雾中的山顶景象吸引而来,但一两周后才发现原来这里下雨起雾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不同于北方普遍的干燥。或许因为「华北屋脊」正在五台山内,即华北地区最高点,而我们寺也在这条脊线上,周边没有更高地势的阻拦,云朵飘到这里时,就被山挂住了。
走在云里,就是走在雾里。我从远处见过移动的云群如何爬过山尖尖;也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见漫天盖地的淡灰色烟来了,包裹住整个世界,一丝一丝的云从伸手处掠过。雾天我也一样地散步,不幸的是我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穿来的是一双很薄的运动鞋,两只脚没有几天是干的,穿三双袜子也只能延缓湿透。


雾有时浓得可怕,能见度只有周边两米,想拍照的话很难对焦。一天我在寺后方的草地,一抬头连寺里那些高大且颜色醒目的殿宇一座都看不见了,完全连轮廓都彻底一点没有。这还是在寺院围墙之内的范围,距离寮房五百米,已经迷路了,我往我认为的来时方向又走了几分钟感觉不对劲,掏出手机地图才发现自己完全走了反方向。还好那天手机有信号,还好再不济还能摸着围墙走一圈——一次安全的小危险。





后来听司机大哥说,冬天的时候整片五台山顶全是巨大的降雪,积雪堆得比人高,非要走只能铲一条仅一人过的窄道,而且雪堆得完全看不见殿堂,一旦失去方向只会越走越远,直到失温。
时间的质感变了,每次四五天的雨雾太漫长到像过了一整个季度,雨过天晴的时候就感觉,好想一直看下去,看到太行山脉的下一个和再下一个季节,看到绿草地从山顶辐射出枯黄色,每一个小山尖积聚薄薄的残雪,再到这一点白色辐射向全世界。
七月底,听闻我的家乡福建刮起了特大台风,这对于沿海人来说本来也不稀奇,但这次有点稀奇,这台风竟然一路北上,直直刮来了太行山脉,导致镇中心爆发泥石流,景区关闭了几天。大风的形状借着大雨可视化了,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真正的自然。徒步行者们全都被迫原地休息,车辆交通更是全部停止,山门一个人都没有。



被濡湿的风马

而我本来就差的手机信号在那几天彻底下线,只有围栏边大概直径两米的地方有一点信号,我顶着满头风雨跑到那里加载好一些文章,再小心翼翼地跑回寮房,生怕一不小心点了关闭。怀疑自己肯定是有网瘾。

台风天的最后一天下午,天空非常突然地转晴了,而交通还没有恢复,我和师兄获准短途郊游一下,去了最近的一个寺院,相传是文殊菩萨曾在此洗澡的地方。来回共耗时四小时,通往该寺院的弯弯小径是我经常对着欣赏的地方,没想到走起来花了这么久。

像这样的短途郊游之前还有一次,一个下午放了半天假,我和两个师兄一起兴冲冲地去往另一个方向的寺院,按我的推想,来回一趟回来还能赶上饭点。一位师兄向我们推荐一口泉,说途中会经过可以顺便去看看。但我感觉绕了好久好久,已经开始累了,师兄一直劝道:「快了快了。前面马上。」马上了十几遍后,终于到了。


这口泉相传是从天界流到人间的唯一一眼泉水,喝了可获八种功德,但他说这泉现在变得好小,以前是很大一池的,可能是因为人间的福德正在逐渐萎缩吧,再过几年可能会消失掉。我赶紧喝了好几口。

在泉水边休息完毕,才正式走上去今天目的地寺院的路途,此时已经傍晚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选择爬最短的直线——一道角度巨大的坡,路上全是荆棘一类带刺的小草。有没有节省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差的体力和心肺功能在此时「发挥作用」,我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上去了,一步一歇,同时心里开始充满了抱怨,为什么师兄前面要那样骗我去泉水,说「很快就到」,结果多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只想着他觉得那里好,不考虑一下同行的人的身体情况吗?如果知道今天要绕这么远,那我就不去了。我的破运动鞋也很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能否回去。
路上的景色变幻,依然充满了从未见过的美丽,但随着我的体能越来越下降,怨气也越来越笼罩着我。回程的路上赤橘色晚霞漫天,我一张照片都拍不动,并且随之而来的就是夜晚。天黑了,我们的照明只有手机,走在黑暗中的山头,我们沉默不说话,很远的风带来马群漫长的嘶鸣。夜晚的旷野诉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中再也难得一遇的场景。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一点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心里只记得生气了呢?
天色是墨黑的了,但天地之间、空气之中还是有微微的光,我没注意到,那是星星的反射。距我们寺院五百米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拖着我我也走不动了,还有一股强烈的怄气,觉得自己会不会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不管不顾地一屁股坐到草地上,垫着包就躺了下去。前面累得只能低着头走路,那一瞬间才看到缀着碎钻的宇宙幕布,月亮有很亮的虹晕,棉絮撕扯状的云飘得比白天慢多了。草地好湿好湿,我能感到我的衣服正在透水。我想,就这样再也不起来也是可以的。
直到一位带着头灯的徒步大叔突然经过,他看到倒在草地上的我和旁边手足无措的师兄,劝我们和他一起走好了。我艰难地爬起来,大叔头灯的强光照亮了接下来回寺院的路,路上大叔说,他就是专门喜欢走夜路的徒步爱好者,晚上没有人。迈进寺院大门,看到了大爷的小屋,我才突然想到,啊,今天本来就不会死的。开始原地大哭特哭。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平时差不多准备睡觉了的点。


后来想想,大概也不能责怪两位师兄,他们很年轻,没有料到我的身体素质会如此之差,而我久在樊笼中,半年之内又阳了两次,也忘却了身体运转的感觉。
像我这样的也遇见不少,走朝台路线只步行的话全程大约需要三到五天,有人穿好了武装到牙齿的一身专业装备,也抵不住扶着膝盖缓缓坐下时的龇牙咧嘴;反而是一些毫不起眼的人令我目瞪口呆,和我同屋住了几天的一位河南阿姨,大红毛衣外摞棉衣,一个不大的双肩包,她说她从景区镇上开始,最远的一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五万多步,遇到寺院就留下来干干活做做义工,直到将整个路线走完。这样的大朝台之路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已经走完七八次了,而她因为睡觉打鼾还说自己身体挺差,我在一旁默默汗颜。
磕长头的朝山者是我最为敬佩的,这个群体也是人数最少的,佛教徒相信,这样三步一拜的过程比步行朝山更为虔敬,福报也更大。不过我想,在这段旅程中,他们在当下即能获得和感知到的,应该比那不知汇率的福报更为广大和深刻。还是说,这就是那更大的福报?他们通常都面色通红或黝黑,脑门上有磕出来的包或护额,话都说得不多,许是因为专心磕头,许是因为累的。磕头大朝台所需的时间还要倍增,假如有点行李的话,背在身上一边磕长头给体力造成的消耗更大,通常他们要先步行到达下一个住宿的地方,放好行李,再折返到还没有磕过头的起始点,重新开始用磕长头完成,假如天黑了还没有磕到今天的住宿点,那么就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再从这里开始。





我遇到过两位结伴磕头朝山的阿坝僧人,行李是一人一个超市塑料袋那么大的折叠包,穿着单层僧衣,膝盖上有护膝,手上两个手套,便是全部了。他们就用这些来完成将近一个月的朝山,然后就回自己的寺院去。前文说提到的两位小年轻师兄,也跟学生春游似地,没有登山杖好鞋任何,一套衣服穿半个月,背个包就走了,山上山下硬造各种小路野路,半个月断断续续走了两三回朝台线。我看到这些人就深感到精致消费主义的愚蠢和失效,也惭愧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之浅薄。




八月底我下山了。走的时候回望寺里的大白塔,分不清我是回到另一场梦里去,还是刚从这场梦里出来。




又或者都是呢?

> 下载少数派 客户端、关注 少数派小红书,感受精彩数字生活 🍃
> 实用、好用的 正版软件,少数派为你呈现 🚀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