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混进投资圈,就开始被人叫蒲凡总了”丨投中吐槽大会
source link: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news/64-20240501-380946.html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可能都很罕见的、title如此密集的时代。
最近在网上冲浪,吃了不少关于title的瓜。一套最常见的剧情是:一位身披着各种光环、拥有饱满个人成绩单的“超级个体”,在即将准备将这些履历进行商业化,进军知识付费或者付费社群产业的时候,忽然被指认这些title名不副实,甚至有严重夸张的成分。
比如去某个知名大厂或者大IP做新媒体运营,可能会被包装成“某百万级新媒体品牌主理人”;比如自己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被某官媒转发,可能会被描述会“作品登上央级媒体”——很多朋友在围观了整个过程后忍不住感叹: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可能都很罕见的、title如此密集的时代。
我对结论持保留态度,因为只要熟读三国的话,就知道其实古人也很膈应冗长title。当年刘皇叔三顾茅庐,第一句就是:“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结果童子直接回呛:“我不记得许多名字。”
但对title密集的恐惧,我确实深有同感。尤其是自从一年多以前,我从宅男气息浓厚的科技内容圈,转移到投资圈之后,在“身份自洽”这件事上适应了很久:为什么创投圈的从业者们会互相称呼“总”?为什么各职级、不同分工的从业者可以自称投资人?为什么有的投资人需要大半页A4纸的title来介绍自己?投资人到底是按照什么逻辑来决定什么title放前面,什么title放后面?
赶巧,咱就借这次机会来好好聊聊吧。
本期研讨会成员:知乎大V&前经纬VP 庄明浩;投资人兼作家 小野酱;投中网总编辑 董力瀚;投中网编辑 蒲凡
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感到尴尬吗?(01:03)
蒲凡:你们平时在对外,尤其是和陌生人社交的时候,你们一般怎么介绍自己?
董力瀚:我先来分享一段经历吧。
前两天为了做《超级投资家》,我去见了朱啸虎朱总。其实我之前跟他见过一两次,但是我估计他印象不深,所以我还是很殷勤地就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我说“朱总好,我是投中的总编辑,我叫董力瀚”——然后我说到“总编辑”仨字的时候我打磕巴了,我有点说不出口。
为什么呢?因为我10年前我在投中就当主编了。那时候我们投中网就是个小破网站,团队只有四五个人。这十几年过去了,公司人多了,团队规模大了,干的事好像比以前格局大了一点,但是我干的还是这摊活。所以我其实还挺不习惯自称“总编辑”的,我老觉得这个title属于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比较合适。
当然了,我刚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才30多岁,现在已经40出头,多少能说得出口了。但早几年走哪都跟人说“我是投中主编,我姓董”。还被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听见了好几次,就老说我“你看他这人,明明是总编辑,结果老说自己是主编,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总之我是对“把总编用在自我介绍”里是多少有点回避的。即使我现在认为,在有必要的时候还是得说,但是说的时候还是会打磕巴,心情还挺复杂的。
蒲凡:你的难以启齿,会不会是因为“总编辑”这个职位现在已经不太存在了?以前的四通立方时代、门户网站时代,一个网站设置一个总编辑职位,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不像现在,很多门户网站已经相当程度地拆掉了编辑和运营团队,杂志和纸媒也很凋零。总编辑,好像是上一代人的职位。
董力瀚:这个概念可能是在变。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你现在去汇报工作,去接受指导的时候,对我们这个类型的企业,有要求建立总编辑制度。就是监管自上而下在规范的时候,尽管目前对我们的定位是一家自媒体,但还是会要求建立总编辑制度,有一个总的负责人,他认为你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个title的人在。
庄明浩:我们公司业务是做社交的,社交公司也是需要有总编室和总编辑。
董力瀚:对,所以我就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总编辑的title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纯粹职业名称了,延伸得还挺远。
蒲凡:庄老师呢?您平时怎么介绍自己?怎么选择您的title?您的title在我看来太多了。
庄明浩:对,其实一直以来,我个人都有一些所谓的title羞耻感。原来还在做投资的时候,自我介绍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投资人”其实是个很宽泛的title。但现在不做投资、在一家企业任职之后,尤其是我们企业的量级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只有在需要代表企业出面,需要以一个非常正式的名义去社交的情况下,我才会使用企业身份。
很多没那么正式的场合,我就会经常纠结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出面。比如,今天一个券商找到我,希望我分享一下近期对某个行业的观察,很多时候我经常用一个类似“某某行业观察者”、非常宽泛的身份来露出。
好在今天有播客了,“播客主播”又是一个更好的、更容易去隐藏自己的title,所以我现在又会经常说我是播客《屠龙之术》的主播,就不会讲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更休闲、更适合开玩笑的场合,我会自谑地说我是知乎的大V。总之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状态,我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蒲凡:所以你是想用宽泛的title来想隐藏自己的什么?
庄明浩:也不是隐藏,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意义能那么拿得出手、当做名片的东西。而且如果对方认识你的话,其实你也不用说太多;如果对方不太认识你,似乎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主动把所有东西展现给对方。这也可能跟年纪有关,咱们也过了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认识也没什么关系。
蒲凡:小野老师呢?你平时对外社交的时候,喜欢说自己是作家还是投资人?
小野酱:我其实有点羞于说自己是“投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投资也没有那么成功,都是跟着大佬们后面走,很多的时候扮演的是把大佬们的事情落地的角色。如果让我说自己是“投资人”,我会非常的觉得羞耻。
每次看到别人出去吹牛,会说我有什么代表作、代表的case。而我却很难说服自己,认为那是我的代表case,我只会把自己定义成,我在里面某项工作里承担了一定的角色。
写作这件事情也是歪打正着的。我坚持写,然后无意中被人发现了,刚好那个时候运气来了,遇到有人愿意帮你出书,一直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的作家。直到出到第四本书的时候,我才问我的编辑,我能称自己为作家吗?我的编辑说,其实你出第一本书的时候都可以这么说了,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感到困惑?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title都是别人赋予的。包括现在策划出新书也好,或者出去进行一些演讲和分享也好,你必须要拿出一个title出来,让别人知道你是谁,所以很多时候也都是主办方或者是出版社帮我去想这个title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反向地用他们给我想的这套title再去设计自我介绍。总之在title这件事上,我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角色。
董力瀚:我想起来当年做“博望志”(董师傅曾经的自媒体创业项目)的一段经历。我们曾经也把稿子编辑成了一本书,委托出版社出版,方便我们到处去约访谈介绍自己,简单快速地说明自己是干什么的、你准备干什么。
有一次和某位访谈对象吃饭,吃着吃着他有位朋友来了。那朋友一看就是一个大哥型的那种人,吭哧往那一坐就问,这哥们谁?然后访谈对象说:写书的作家。
我当时很客气,说别,不是作家,我撑死算个作者。访谈对象也就顺着我说,对,作者。大哥就看了我一眼,后来那饭桌上就再也没搭理我。我估计他心里想,什么作家、作者,神经病,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楚。
反正这种事很扭捏的。
小野酱:我也特别有感触。我出第一本书之后,我说自己是写作者,因为我总觉得作家应该像鲁迅那样才能称之为作家。
但是在这个场域里面呆久了,你会发现你不开口,你可能就是桌子的调剂小菜。所以title必然会更多以被动的形式产生,因为它的浮夸、它的存在,其实是邀请你的人,他也想通过你的社交杠杆来证明他是一个有素养的人,或者对外证明看我的社交圈很有文化。所以之后别人再叫我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创投圈为什么喜欢互相称呼“XX总”?(11:15)
蒲凡:那你们觉得创投圈是一个title比较膨胀的圈子吗?虽然各行各业都需要title,但我个人体感而言,好像投资圈更严重。
我以前做科技内容,2022年下半年加入投中之后开始做创投内容,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叫你“总”——我自己内心很明白,无论是从我的职级也好,还是从我的工作内容也好,我没有哪个环节称得上“总”,但是大家就是习惯叫你“总”,而在之前在科技圈,好像大家都习惯叫你“老师”。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老师”这个title也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称呼我为“老师”首先冒犯了老师这份职业,第二是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你什么,或者是真的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值得你的尊重。但创投圈开始频繁叫“总”,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现在大家随便叫我“老师”我都无所谓,甚至觉得叫“老师”这个称呼很亲切。
小野酱:“老师”这个称呼很温和,就像一个无性别或者是无任何情绪导向的标签,又有半分尊重在里面。
蒲凡:对,所以我就很疑惑,创投圈是为什么会养成一个互相称之为“总”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野老师你喜欢别人叫你野老师还是叫你野总?
小野酱:我其实都很习惯,因为我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家的称呼都是以“总”互相称呼的,对这个称呼已经被我的生活消解了、祛魅了。
蒲凡:但家人之间都是戏谑地叫吧?
小野酱:对,戏谑。还有如果父母做生意的话,父母周围的朋友也大部分是什么“总”。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叔叔天天跟他吃饭,他喝完酒也不就那样,他也是个“总”,啥啥都是总,你就会对这个称呼完全没有什么多余想象,没有什么滤镜,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的习惯。
加上我特别能折腾,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带cosplay出去商演,去接触举办商演的大型商超。一般对方就会默认你是一个“总”你是一个老师,因为你不是个学生,他才能在同一个对话体系里面跟你对话。虽然那个时候我也会心里怯,但是多参加几次比赛、商演,你就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会暗示自己要跟这样的人谈判,我要有这样的底气,然后你就能自然而然地接受别人叫你什么,你就被逼真进入商业文明里。
蒲凡:但是你不会觉得,如果别人叫你“总”是对你一种气质上的定义吗?因为我是觉得“总”这个称呼太商业、太名利场了,别人一喊总我的脑海里就会泛起白酒味,脑补出酒楼那种特殊的气味。
董力瀚:我觉得对方怎么叫你,其实是取决于他自己,而不取取决于他对你的看法。他如果要叫你“总”的话,是他认为在他的语言环境里边叫你“总”比较合适的,而不是说他觉得你长得像个“总”。
庄明浩:对,我的口头禅有一句是“不要叫什么总,叫我明浩就好”,这是一句已经非常常见的口头禅了。
蒲凡:但是大家也会忍不住叫你明浩总。
庄明浩:年纪大了,这个没办法避免。而且当在公司里就更没办法,因为公司里有真正意义上的职级。但是在外面,尤其当陌生人拉个群,介绍一些商业合作之类的,很多人会比较客气的,在微信里叫明浩总什么的,我一看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可以不用叫什么总,叫我明浩就行。
阶段性地“title膨胀”,是有好处的(15:31)
蒲凡:咱们四个应该都是一种人,就是对title有耻感。我的理解是,对title的耻感是因为我们把title当做了一种职业标准。
我就经常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的职位,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份职业实际上是有正式的职业资格证、有机构认可的。其次,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比肩那些我心中的榜样。第三,我写的内容也不纯粹是像我们传统认知里,媒体所需要完成的那些职能,比如媒介传播、信息传递,或者舆论监督等等——这一切我都达不到的情况下,我就不好意思叫这个字。
但对于title的羞耻这件事,其实是让我吃过大亏的。
2022年夏天,我因为之前的团队解散被迫开始找工作,那也是我7年以来第一次找工作。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董老师。那段时间怎么说呢,因为团队被迫解散等一系列的糟心事,我对我自己的工作能力很不自信。再加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找过工作了,我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总结自己。
那时候,我的很多前同事也在找工作,他们的心态和我大致相同。直到最后大家都安定下来,我们彼此一闲聊才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其实是严重低估的,低估到无论是职级还是预期的薪资都自我压抑到一个很低很低的状态。
所以我后来在想,定期复盘或者说定期扩写自己的title,实际上是可以给自己争取利益更大化的一个有效策略。
董力瀚:你是对投中现在的薪资很不满意吗?
蒲凡:很满意,我是对我之前的薪资待遇不满意。设想一下,如果按照咱们最近吃瓜看到的那一些经验,我完全可以把我描述得很浮夸,毕竟自媒体主理人我干过六七年,拿过不少奖,也有不少爆款,其中一些爆款还会得到罗永浩这些顶级KOL的下场回复。
但我没有浮夸地描写这些,我拒绝了,直接导致我的每月基本收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4位数。所以2022年我找工作那段时间,当我把这些事儿分享给一些朋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傻逼,因为自己不善于膨胀,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亏。
庄明浩:title膨胀这件事也分人、分性格、分阶段,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跟错。今天咱们几个都是偏这一边的,那世间既然有偏这边的人,就一定会有偏那边的人,有极端会偏那边的人,所以我们必然会看不惯那样的方式。
但是在某些人生阶段进行阶段性的总结确实是必要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求职,你要换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选择。这有些类似我们做投资去跟创始人聊,很多创始人去跟投资人沟通的时候,会或多或少地放大自己的工作履历跟title,这是人之常情,大家也都理解。适当的美化,因为你有所求。
蒲凡:以当小野老师她有心要运营自己IP的时候,我一直建议她把自己的title顶格拉满,按照标准所处最大的象限来描述自己。因为我发现她也是这种性格,因为自己不善于总结title吃了很多暗亏
小野酱:我也是看到最近别人会把自己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的东西,包括自己参加过的大型活动都写出来,拿来当招牌,我才开始反思,之前是从来不写的。
之所以有这种心态,或许是因为相较于当下这个周期,过去大家太忙了,你会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很快就忘记了,不会把它当回事。你也会很坦率地承认,只是因为你运气好、时运好,并不是能力至此,也不会特别当回事。
有时候我也会想,说如果我也是那种性格,把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包装出来,我现在的状态会怎样?很难说,总觉得说不定自己到现在已经翻车了。所以我开始坦然接受认知不足、运营能力不足,也承认自己心力不足,就算有泼天的富贵或流量来了也接不住。
不过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你做过很多事情,只要你能坚持下去,可能有一天你就会被别人发现你的光和热,甚至会有人愿意帮你发扬它的光和热——就像张磊说的,“流水不争先,争得是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更关键,甚至我会把滔滔不绝理解为“超越个体生命的滔滔不绝”。
不管是创投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如果你有一个东西能超越你生命长度的,你走了还会有人记得的,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当下我挣那个块儿八毛。很多人太在意那块儿八毛的事情,反倒会有一些反噬的效果。所以我经常会干一些没有金钱回报、更像是在耕耘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要能够马上获得巨大的商业反馈,但是他们可以激发你,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更多面,所获得的东西超越我做一场主持或做一场演讲拿到的几千到一万的车马费。
而且你也因此种下一个种子。虽然不知道这些种子能会回馈给你什么东西,但很多时候是惊喜的。比如我会遇到有些读者在5年后、10年后找到我说,小野老师你知道吗,当初就是因为听到你的某句话,我最终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比当时的现金收获更有价值。
人在什么时候会去积极地“争取title?”(23:35)
蒲凡:所以我能不能下个定义,膨胀title是用来兑现已有的经历,克制title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可能性?
小野酱:可能还有对成功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成功的标志,就是我能扬起我的镰刀,去割这帮韭菜,但我不并不这样认为。
蒲凡:我突然想问你个问题,我推荐你去报名【某个榜单】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小野酱:我其实还是抗拒的,因为能够从我的熟人圈获得很多正反馈,不需要一个劲地跟别人PUSH的说我是谁,我干了什么,我很厉害,我优秀死了,你们都来跟我合作。所以我的心态就是“试试看”,就是能上就上,不能上也不勉强。
董力瀚:我觉得title就是一种社交货币。你用还是不用,你吹还是不吹,很多时候就是跟着需求走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单飞单干的人需要title,然后你在一个大公司里去做执行——比如我和蒲凡——就不需要,然后庄老师偶尔需要、偶尔不需要,小野是特别需要,咱们四个的需求层次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我也一直认为,title的展示就是一个品牌行为。我个人理解,品牌是用来忽悠【大笨蛋】的,不是用来争取行家或者是同行认同的。就是如果你做的生意,做的买卖、做的业务,需要和你相同层次的人,或者同一个小圈子里边的人就能把事办了,把钱挣了,你就不需要去做过多的title展示。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让更多的人、不明就里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品牌好高级、好厉害,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再去割韭菜也好,再去变现也好,你就一定需要把这东西吹得大一点、再大一点,体面不体面我无所谓,你先把这个事办了,对你有经济价值。
蒲凡:适度title吸引异性,过度title吸引同性?但是董哥,我司作为给别人发title的机构……,这两年你有感受到大家对于争取title的热情是否有变化?
董力瀚: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发的不是我刚才所谓的“品牌行为”“社交货币”,我们发的其实是小圈子里边的信用背书,这个可能跟传统意义上的title还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很多title膨胀所引发的问题,但大量的场景是自己给自己加title。一个是行家、一个专业的,无出其右的第三方对你的认可,和你自己把自己包装成XX师,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蒲凡:其实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我觉得对于寻求title的热情,可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家的近况。比如说大家如果积极寻求title,那就说明现在整个行业内卷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竞争愈发困难了。如果对title非常不care,那就说明行业非常舒服。
我遇到的一些极端情况是,我只能跟某人聊聊,然后回头你就看到他说他“接受了投中网的访谈”,变成了他简历上、title里的一部分了。
庄明浩:访问这种东西也能变成title?也太雷了。
蒲凡: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能在进行他描述的这种行为。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下,我的职级就特别重要了——他们会跟其他人介绍说,这位是投中网的副主编,专门来我们这儿实地考察,然后顺便对我们整个园区或者是整个计划进行一系列报道。
你看这里面出现几个词,副主编、园区调研,然后进行系列报道,就是把我只是过去玩一玩这个行为拔高到象限的最顶层,然后就觉得好惶恐。这里面也包含着对我一个预期,就是希望我为他干一个什么事情。否则的话,他大可以说成一个哥们过来串串门。
董力瀚:都是物尽其用,就是跟着自己的需求尽量多薅你一点。
蒲凡:对。所以我觉得人们对title的热情和行业环境也高度相当。刚才聊到2022年找工作的时候,我系统地总结了一下个人title。其实在团结解散之前,我同样为团队系统地总结了一遍title,因为那时候我需要拿着title去说服大企业,去说服潜在的广告主,说我能干成什么事,有这么一层表象作用。
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就是当你换了一张牌桌以后,你的title的展示权就不在你手里,而是根据牌桌上原有的主人喜好来决定title。
比如当时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想投资我们的成都本土文化产业集团,他们的老板很喜欢某个【知名内容平台】,于是他们就老问我,你在【该内容平台】上面的阅读量能达到多少?
说实话,我从业这么多年,其实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数据,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那阅读量这东西是网页数据,随便改;另一方面就在于怎么说呢,该平台在我的概念里也不代表一种筛选标准,因此我从不在意他是否会转载我的稿子、会有多少阅读量。
但是那个时候团队揭不开锅了,我必须要换一张牌桌的时候,当他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自然而然地去把我在这个平台上获得的奖项,在这个平台上取得的数据,总结出来放到了PPT里面。结果我发现当我换牌桌了以后,我的对外title展示的主导权都不在我了。
这种感觉也不能说失落,但也挺别扭。
董力瀚:所以你看,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好多人要拿一整页纸来写自己的title,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一群什么人,他们的需求有可能是什么,我尽量多列一点,说不定有哪一个我能打到你。比如说你要当时写了一个A4纸,满满当当的title或者履历的话,没准就能命中产业大佬的一个点,新的预算就有了。
蒲凡:但我后来又发现,按照对方的喜好来决定title也没用。因为人家主导,就相当于人家点菜了,评判权在人家、评判范围也在人家。他想吃鱼香肉丝,我就必须做鱼香肉丝来决胜负,我只有这一种选择,我擅长做青椒肉丝是没有用的。
董力瀚:哥给你一个劝告,就是四字箴言“不要下桌”。你只要不下桌,你不会那么卑微的。
什么样的title值得警惕?(36:33)
小野酱:整个时代的title泛滥,也说明了商业环境变化。以前是所谓的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以前可能话语权高度统一,你做一个特别大型的活动,能请到的嘉宾只有为数不多的选项。等到商业社会足够发达,选项变多了,更多的人需要去竞争有限的机会,这时候就需要很膨胀的title能为自己带来引流。
所以我那天就写了个段子,我说马云只要说“大家好我是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就好了。但是中段的人、那些期待有人买单的那些人,他们身在所谓买方市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快速的搏出位,可能title的膨胀也是一种搏出位的方式。
董力瀚:你对马云的定位肯定是不精准的,他怎么会需要后边那几个字呢?
我见过最厉害的名片,是【某知名天使投资人】,就仨字,他的名字。那会大哥在微博上火得不得了,怎么可能需要解释我自己。
蒲凡: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咱们最后谈两个非常实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各位觉得什么样的title值得警惕,或者说坑的title有哪些共同特征?
庄明浩:我在录这个话题之前,想起一个当年我见过印象最深刻的title,这个title我已经记了十几年了,来自国内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一位独立开发者。他在社交平台上的title写:与奥巴马互关。
这个title我真的我会记一辈子的。
蒲凡:这个太有微商思维了,当年每个微商好像都有一个跟奥巴马或者特朗普合影的照片吗?
庄明浩:再有一个最近我印象比较深的title来自即刻,title写着ex腾讯,逗号,创始人,我当时看到第一眼真的是生理反胃的感觉。
董力瀚:他想误导你?
小野酱:如果是有意的误导,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蒲凡:小小野老师呢?你遇到过哪些值得警惕的title?
小野酱:我反正觉得所有冗长的title好像我都会比较警惕。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某一个垂直细分领域有一些成绩的话,你就不需要那么的大声呐喊,可能越喊就说明你越没有。
可能也是因为我周围的人通常来说都不这样,所以就会让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或者说跟我玩得好的,或者我认可的人他都不那样,所以我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个人发给我东西特别长,特别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有点问题的,他急于要向我证明什么,可能代表着他交付的能力是不是也比较差。
蒲凡:我是觉得新词越多的title越值得警惕。庄老师刚才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例子,你会发现他使用了好多新词,就是传统的职业好像概括不了他,他就非得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在一个独立的场域里面来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
小野酱: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我读不全的感觉,我都读不懂。
蒲凡:对,你一定要警惕这title里面包含了大量你读不懂的新词,或者干脆这就是他新造的词。
董力瀚:我前几天在微信群里遇见一姐们儿,刚进群也发了一整页title。这都没什么,但其中有一个title我看了为之一振,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还原了,大概title的意思就是说她是“制造镰刀的人”。
我当时觉得,现在他们那个圈子,收割的层次、结构已经复杂到你直接可以当镰刀的镰刀了,非常直接了,都不用假模假式地说我面对一帮韭菜,偷偷地当镰刀,而是说我是一把老镰刀,然后我教你们怎么做镰刀,你们谁觉得自己是镰刀的过来让我收割你们。
蒲凡:对,而且你会发现它里面包含了一种我以身为镰刀或制造镰刀为荣,不仅是没自身耻感,道德耻感也没有了。
董力瀚:隐藏的话就是我这样是可以搞到钱的。你们不是都想当镰刀搞钱嘛,我可以带你们搞到钱。
小野酱: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广告页,就是一门写作课要收费22000元。
蒲凡:对,这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点,就是title里面数字大到夸张,你一定要去较真一下。比如说昨天小野老师给我看到的写作课广告,它里面有一个title说该小说畅销30万册——我当时虎躯一震,就在琢磨现在一本纸质书小说居然还能买这么多,真的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作家的名字。所以我就去问小野老师,30万册是一个出版业的什么标准?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小野老师作为接触过出版业的,才告诉我什么样的书才能在这个时代卖成这样的结果。
董力瀚:年度畅销书?
小野酱:第一是年度畅销书,还有一种是那种地摊文学,在那种村镇、四五线的借书摊或者是卖书摊特别多,这也是出版社老师告诉我的,是重生系列、穿越系列、玛丽苏文学的变种,有一些出版社专门以卖此类书号为生,你在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或者好一点的书店都会看不到的,但在地摊上面到处都是,也很便宜。
蒲凡:对,所以你看如果对title不较真的话,真要交2万块钱去学习写这种书的写作课,我真不知道能学出什么。
如果title需要克制,那么需要克制到什么程度?(48:05)
蒲凡:一定会有不少的职场新人,或者是正在对自己事业抉择的人,在苦于如何梳理自己的title,咱们觉得对于title的描写需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问题背后,就是三位在选择自己title展示的时候的逻辑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是否有参考价值?
庄明浩:我觉得还是跟性格有关。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去讲自己的title,可能确实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每个人对于阶段性要什么,阶段性想表达什么,阶段性希望别人对你的认知是什么是有期待跟期许的。
这个无关对错,只能反过来讲,最近一连串的风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样的传播跟舆论,甚至到了一种大家群起而攻之的状态,可能还是说明很多人之前就看不惯,大部分人其实都对于这件事情是像我们一样有羞耻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不是这样。我还是那个观点,阶段性想清楚自己做这个方式能够为自己带来什么,在过程中你可能会失去什么,你想清楚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了。
小野酱:我觉得是很多人想清楚了,我要靠这个干成什么,但是问题就是说它中间不可控的风险他忽略了。
蒲凡:也有可能不是忽略了,他就觉得收益大于风险,他就这么干。
董力瀚:我有两个逻辑,一个是你自己的接受程度。咱们几个一说自己的title都还挺害臊的,这个其实是你首先需要克服的第一步。我对这事的想法就是,我如果要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总编辑”,甭管人家知不知道投中网是干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对方会对你有一个所谓总编辑的设想、概念,想象应该是那样的,然后你就会特别害怕,你达不到对方所设想的标准,然后你这句话说的时候有问题,因为title其实不是讲给自己听的,你是讲给对方听的。
其实我们的商业文化里,大家通常都会把title定得稍微高一点的。你只要在这个游戏规则里边,别人都高,你也有必要要稍微的听起来有想象力。只是这个心态调整就很麻烦,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得了的那个东西,你只有先学会接受才能再用它。
然后第二步就是根据需求,你想好你这东西是给谁听的,他听了之后是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比如说像咱们这种打工的,你其实不太需要这个东西,你只需要在一个小圈子里边兜圈子,告诉人家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认为我的答案跟野总答案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最起码需求是完全不一样。
小野酱:我们到底为啥不一样?
董力瀚:你还是不接受现实对吗?我觉得你要当一个自力更生的女老板,你必须得走这个路。
小野酱: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思考了其实挺多次的,每次别人非要让你把自己介绍捧特别高,这件事情我其实思考很多次,特别是在一些不是我熟悉的语境,比如说海外的语境,比如说香港的语境,比如说在英国的华人语境,在这样语境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大部分时候来以我要达成什么结果来判定我现在要露什么牌。
当然我本身还是更愿意藏,而不是更愿意去暴露自己,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是那么的厉害。可能有一天比如说我到40岁或者5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出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以认可我自己,我可能会更坦然一点。但现在我可能还在爬坡的阶段。
蒲凡: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2022年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得不被逼下牌桌的时候,你就会给自己列title了。
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你能如愿到当你40岁50岁取得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选择包装自己的title,应该还是在你个人可控范围之内,而不是无限膨胀。只有当你被逼上绝路,你的title包装就无上限了。
小野酱: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我就不一定说非要去要靠我的title去干嘛,这个世界上大量的普通人。
蒲凡:那说明你还有退路。
小野酱:我不觉得现在我们目之所及很多让自己title膨胀的人是没有办法、没有退路的,而是因为他期待在短时间内更快速的收割韭菜,以及获得更大价值,他很怕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快就流失了,或者说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割不到韭菜了,或者我赚不到这个钱了,他有一种急迫感要证明自己或者说要赚到这个钱。
仔细想想,其实他们也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不靠title,我就是勤勤恳恳的写东西、写报告、做一个普通职员。可能每天做word、做Excel、做PPT,你也能过,只不过我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个叙事逻辑,让别人pay attention在我这里,关注到我,我要发声了,我要说话了,我要开始赚钱收割韭菜了。
蒲凡:刚才董老师好像想插嘴说啥?
董力瀚:我刚才是想说你可能今天收尾还是得用四字箴言“别下牌桌”收尾,你们一聊就总会聊到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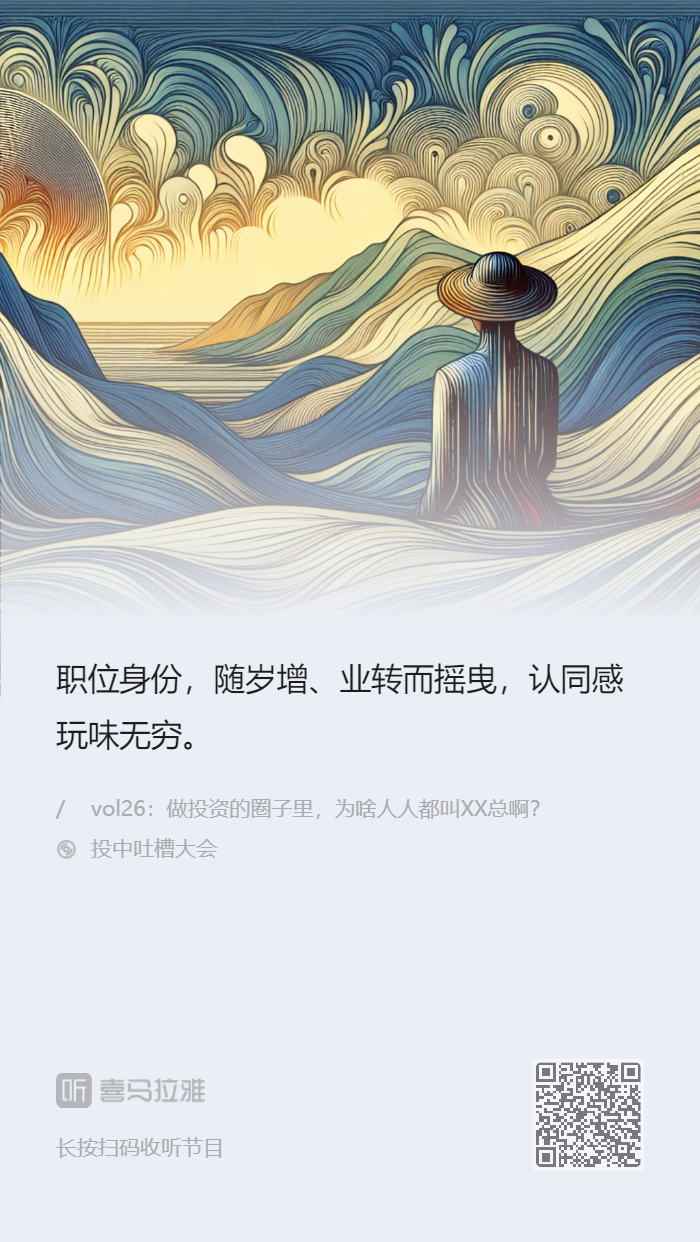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