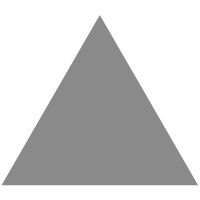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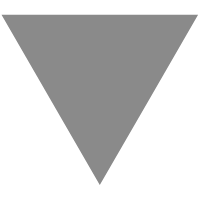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尼采笔记II
source link: http://sht2019.cn/2021/09/23/270.ni-cai-bi-ji-ii/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尼采笔记II
2021-09-232021-09-23 字数: 10.8k编号: 270
Friedrich Nietzsche - Wikipedia
在我刚刚接触某些哲学家的时候,会去看看网络上对于哲学家的评论和一些论文。
我受过其误解。不过按尼采先生的话说。在网络上,这些是市场上的苍蝇,
不要再抬手去打击他们!他们是数不胜数的,而你的命运并不是成为蝇拍。在论文上,是一些咿呀的驴子,有相当多的作者总是写某某认为,他们不是为学术自由写作,而是:
阿们!让赞美、荣耀、智慧、谢恩、奖赏和力量归于我们的上帝,无穷无尽!
——而驴子于此叫了一声咿呀。在网络上还有相当多人的对哲学的认识不过停留在文字感情上面,一听到唯心便想到迷信,
一听到唯物便想到真理。’唯心’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唯心’的,就连唯物的基本实验行为都没做到,
就胆敢自称唯物,靠的全是习惯了,习惯了说唯物,人们从小被教育说唯物,成了习惯的奴隶。
抛弃你们对一切事物的偏见,勇敢的去行动,这些人才能进一步的了解世界,
而不是停留在一些肤浅的多数人感情上面。【关于勇气我想说,一旦得到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不要胆颤。】
人们总是用文字限制他们的认知,用文字把无限的东西想象成他们的感情,天空本身是无限的,
人们却用天空两个字简单概括,关于天空还有着无穷无尽的知识等着人类去发现,不要停滞啊!人类。
《1960权力意志》
1885年4月至6月
34[30]
我们身上的感官之感知是无意识地发生的:被我们意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是被加工过的感知
34[36]
真正说来,“信仰”问题就是:本能是否比推理更有价值?以及为什么?
在关于“知识与信仰”的诸多争执当中,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隐瞒了这个估价问题。
苏格拉底幼稚地拥护理性而反对本能。(但从根本上说,他却是服从一切道德本能的,
只不过带着一种错误的动机说明:仿佛动机是出于理性的。柏拉图之类亦然。)
柏拉图不由自主地寻求一点,即:理性与本能意愿的是同一个东西。
直到今天的康德、叔本华和英格兰人也是如此。
在信仰中,对最高权威的服从之本能被置于优先地位,也就是一种本能。
绝对命令乃是所想望的一种本能,在其中这种本能与理性是一回事。
34[54]
相反的时间秩序。
“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向大脑发出信号,在那儿得到整理、成形,
被归结于它的原因:然后原因被投射,于是事实才为我们所意识。
这就是说,现象世界只有在“它”已经起作用,而这种作用已经得到加工处理之后,
才作为原因显现给我们。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断地颠倒了事件的秩序。
——当“我”观看时,它已经在看某种不同的东西。有如在疼痛时的情况。
34[55]
对感官的信仰。如果有我们的理智的基本事实,那么,它就是从感官中接收它要解释的原材料的。
从道德意义上考察,理智对待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受真理之意图引导的,
而是由一种求征服、同化、营养的意志来引导的。我们持久的机能是绝对自私的、
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毫不迟疑的、精致的。把命令和服从推向极致,
从而能够完全服从,个别器官就有了很大自由。
目的信仰中的谬误。
意志——一种多余的假设。
相反的时间秩序。
对因果性信仰的批判。
对感官的信仰乃是我们的生命的基本事实。
核心—强力——本质上不允许与它所统治的东西区分开来。
发生史不能说明特性。后者必须已经得到了认识。历史学的说明乃是一种还原,
即还原到一种我们所习惯的彼此重叠(Aufeinander):通过类比。
34[66]
总是反讽(ironice):看着这样一个真诚的思想家,这真是一种可贵的感觉。
但更惬意的是发现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他根本上意愿某种不同的东西,
而且其意愿方式十分鲁莽。我相信,苏格拉底的魔力在于:他有一个灵魂,
背后还有一个灵魂,那背后还有一个灵魂。在最前面那个灵魂中,躺着色诺芬,
在第二个灵魂中则是柏拉图,而在第三个灵魂中仍旧是柏拉图,
但却有着他自己的第二个灵魂的柏拉图。柏拉图本身是一个有着许多暗洞和表面功夫的人物。
34[67]
注意!就其最根本的本能而言,我们时代乃是怀疑的:
几乎所有比较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是这样,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
悲观主义,说不(Nein-sagen)只是更容易让精神感到舒适:
我们这个弥漫着民主空气的潮湿时代是尤其舒适的。在精神比较娇弱敏感的时候,
它就说:“我不知道”,“我相信自己,再也不信任何人了”,“我再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还去往哪里”,还有“希望——”,这些都是说谎者或者煽动性演说家和艺术家们的惯用语。
怀疑——是某种生理学特性的表达,这种特性在许多物种大杂交的时候必然会出现:
许多遗传下来的价值评估是相互冲突的,阻碍着彼此的发展。
在这里最缺失的力量就是意志:因此,对于责任有大恐惧,
因为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躲在集体后面,这就叫“滥竽充数”。
于是形成了一个群盲种类:谁若具有一种强大的、命令性的和大胆的意志,
他就一定会在这样的时代里获得统治地位。
34[68]
人们抱怨,迄今为止哲学家们搞得多么糟糕:真相是,在任何时候,
一个强大的、狡诈的、放肆的、无情的精神的教育的条件,比今天都要有利些。
在今天,教唆者之精神,也包括学者之精神,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人们且来看看我们的艺术家:是否他们因为一种放纵差不多全都会走向毁灭。
他们不再变得专横暴虐,因而他们也不再学习对自身施暴。
女人们何时像今天这样低微啊!一切都变虚弱了,因为一切都意愿搞得更适意。
——我经历了身体痛苦方面最严苛的训练:而且意识到已经把自己固定在其中了,沉默无语——
34[70]
休谟要求(用康德的话来说)理性给他一个说法和答案,
说明理性有何种权利思考自己:某物可能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如果它已经被设定,
那么由此必定也有某种不同的东西必然被设定,因为原因概念说的就是这个。
休谟毫无矛盾地证明了,对于理性来说完全不可能先天地(a priori)、
根据概念来思考这样一种联系,如此等等。——但愚蠢的是,
去追问论证之合法性的各种理由。他所做的正是他想要检验的。
34[74]
人的境界。人们可以把哲学家理解为这样一种人,即他们极其努力地去考验,
人能够把自己提升到何种境地,特别是柏拉图:他要考验他自己的力量能达到多远。
然而,哲学家们都是作为个体做这件事的;也许恺撒这种帝国缔造者之类的人物的本能更大,
他们想的是,在进化过程中以及在“有利情况”下,人可能被推进到多远。
但他们没有充分地理解,什么是“有利情况”。一个大问题:迄今为止,
“人”这种植物在哪里得到了最绚丽的生长。为此需要做一种历史比较研究。
34[75]
值得注意的是,斯多亚派和几乎所有哲学家都看不到远方。
还有就是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总是仅仅代表群畜的需要。
34[86]
词语乃是概念的音符:但概念是重复的、一起发生的种种感觉或多或少可靠的组合。
人们相互理解,这还并不意味着人们使用了同样的词语:对于这种内在体验的同一种类,
人们也必定需要同样的词语——人们必须共同拥有这些内在体验。
因此,同一个民族的人们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如果人们长期在类似的气候、
活动、需求条件下一起生活,
则某个种类就从这些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切近易解的体验中获得一种优势:
快速的相互理解就是结果。结婚和遗传也是个中结果。正是那种需求,
那种让人快速而轻松地理解自己需求的需求,把人们最牢固地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发现大家以“友谊”、“爱情”之类的词语意指不同的东西,
则关于友谊、爱情,就没有什么可固定的。因为何种感觉组合处于显突地位,
这一点乃是价值评估的条件:但价值评估乃是我们最内在的体验的结果。
这样说是为了说明,为何要理解像我的著作这样的文字是困难的:
内在的体验、价值评估和需求在我这儿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多年与人们交往,
极大地推动了断言和礼貌,以至于我从来不谈我内心的东西。
是的,我差不多只能这样与人们一道生活。——
34[87]
我们想象,在我们的意识中隐藏着命令者、最高首长。说到底,我们拥有一个双脑:
我们有能力去意愿、感受和思考我们的意愿、
情感和思维本身——我们用“意识”一词来概括这样一种能力。
34[88]
注意!那些立法的和专横的精神,他们能够把一个概念固定起来,抓住一个概念;
那是一些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意志力的人,他们懂得把变动不居的东西、精神长期地石化,
差不多使之永恒化;这种人乃是最高意义上的发号施令的人:
他们说“我想知道这个那个已经被看见了,我就要它这样,我就要它为此而且只是为此”。
——在任何时代,这种立法的人都必然地发挥最强大的影响:
人类所有典型的提高和布置都要归功于他们:他们乃是塑造者(Bildner)——
而其余的人(在此情形下即绝大多数人——)则与他们相对立,只不过是砧板上的鱼。
34[92]
人们感谢基督教会,盖有两条:
1)一种对暴行的神灵化:与罗马圆形竞技场那种壮观的、但近乎愚蠢的屠杀相比,
地狱观、刑讯和异教徒法庭、火刑之类,还算是一大进步。
这种暴行中还包含了许多精神、许多隐念。——它发明了许多乐趣——
2)它借助自己的“不容异说或不宽容”,把欧洲人的精神弄得精细而灵活。
人们马上就会看到,在我们这个拥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民主时代里,
思想是如何变得蠢笨不堪的。大家注意听哪!——是德国人发明了这种炸药。
但他们又与这种炸药断绝了关系:他们发明了新闻出版业。古代城邦正是这样来计划的。
相反地,罗马帝国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上给予很大的自由,
比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度都要大得多:后果立即就有了,就是精神的巨大蜕化、
蠢笨化和粗糙化。——莱布尼茨、阿伯拉尔、蒙田、笛卡尔和帕斯卡尔,
他们看起来多棒啊!看到这些人物灵活的大胆鲁莽,乃是一种享受,为此我们得感谢教会。
——教会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本质上是不屈不挠的、严苛的,拜这种压制所赐,
概念和价值评估就被处理为固定的、aeternae[永恒的]。
但丁由此赋予我们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人们绝不需要受一种绝对统治的限制。
如果存在着限制,那么,这些限制已经被拉伸至一个巨大的空间范围,感谢柏拉图!
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十分自由地活动,有如巴赫之于对位形式。
——如果人们彻底学会了享受这样一种“法律之下的自由”,
那么,培根和莎士比亚就几乎要令人作呕了。与巴赫和亨德尔相对照的当代音乐亦然。
34[108]
我把民主运动看作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但它并非不可阻挡,而是可以延缓的。
然而大体上,群畜之本能和群畜之评价的统治地位、
伊壁鸠鲁主义和彼此的善意将日益增强:人将变得虚弱,但良善而和气。
34[161]
注意!一位能工巧匠或者一位学者,如果他很为自己的本事自豪,而且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那么,他看起来就会非常好;而且,他不会悲苦地看待任何事情,
而那些马虎行事者或者教书匠们,则整天苦着个脸,想让人明白,
他天生真正可以做些更好的事。根本没有什么比好更好的东西!而这种好就是:
具有某种卓越性,根据这种卓越性去创造,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讲的virtù[德性]。
1885年5月至7月
35[19]
人们必须摆脱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有同情心的?
——而是要追问:“什么是这个好人、这个同情者?”
35[25]
问题:许多伟人种类也许已经不再可能了?例如圣人。也许还包括哲学家。
最后还有天才?也许人与人之间惊人的间距关系已经被削弱了?
至少,这种间距感已经减弱了,带来的效果是一种较少粗暴的态度和规矩,
由于后者,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拔得那么高了。
——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人之伟大性的新概念;我们有能力做到这种伟大,
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与这种伟大鸿沟相隔了。瞧,
这个民主世界把每个人都转变入一种特殊性之中,所以在今天,伟大就是成为普遍。
它削弱意志,所以在今天,意志之强大就是伟大。它培养群畜,所以在今天,
独立和自立被看作伟大。最广博的人特立独行,没有群畜本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意志,
这种意志使之变化多端,永不餍足地潜入全新的生命深处。
——我们必须在我们最少有在家之感的地方寻找人之伟大。对能量时代来说,
那种温柔的、断言的、安逸的人是一大特例;这种人具有伟大的内在的风纪和严苛,
方得以从一种半野蛮的动物变成一个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的漠然冷淡差不多有一种美化的效果。
我们则得出相反的理想:而且首先我们必须为自己捣毁那些旧理想。
35[35]
我与形而上学家最彻底的区别在于:我不承认他们的说法,即所谓“自我”就是思维者;
相反,我则把自我本身看作一种思维结构,具有与“质料”、“事物”、“实体”、“个体”、
“目的”和“数”同样的档次,也即都只是作为一种规整性的虚构,借助于这种虚构,
某种持存性(因而“可认识性”)才得以被安插——被构想——入一个生成世界之中。
对于语法的信仰,对于语言主体、客体的信仰,对于行为—话语的信仰,
迄今为止都征服了形而上学家们:我则要教人们断然放弃这种信仰。
是思维首先设定了自我:但迄今为止人们都相信——像“民众”一样——
在“我思”(Ichdenke)中包含着某种直接的确定的东西,
这个“自我”就是既定的思维之原因,以此类推,我们便“理解”了所有其他的因果关系。
现在,无论那种虚构可能多么寻常,多么不可或缺,都丝毫不能否定它的臆造性质:
它可以成为某种生活条件,但尽管如此它依然是虚假的。
1885年6月至7月
36[2]
对于有生命的创造物,除了关于它们在陆地上的起源之外,从来都不曾有更多的期望:
它们先前习惯和适应了在海洋里的生活,
在陆地上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和习性转变和翻转过来,
在所有方面都不得不做一些不同的事,不同于它们以往干的——迄今为止,
地球上没有发生过更奇特的变化。——正如在当时,通过坍塌,通过地球的一种缓慢的崩溃,
海洋沉入断裂、洞穴和沟槽之中,获得了深度;同样地,如今在人类中间发生的事,
用比喻来说,也许给出了与之直接相反的情况:因为人之变得整体和完整,
断裂、洞穴和沟槽的消失,因而——稳固的陆地也消失了。
对一个人来说(我的思想方式已经把他搞得完整而整体),“一切皆在海洋中”,
海洋无处不在:但海洋本身已经失掉了深度。——但我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比喻,
只是迷路了!我想说的是:我与每个人一样生为陆生动物——尽管如此,现在我必须成为海洋动物!
36[8]
道德
自古以来,人类在对自己的身体的深度无知中生活,满足于若干个能传达自己状况的公式,
同样地,关于人类及其行为的价值的判断也是如此:人们靠自己抓住某些表面的和次要的符号,
没有感觉到,我们对自己是多么无知和陌生。就关于其他人的判断而言:
这个最谨慎和最公道的人在此还是多么快速而“肯定地”做了判断啊!
36[21]
弱者渴望成为强者,乃出于营养困难;它想要躲避起来,尽可能与强者成为一体的。
相反地,强者则要防备自己,他不想以这种方式走向毁灭;而毋宁说,
他分裂为二,甚至分裂为更多。求统一的欲望越大,人们就越是可能导致虚弱;
求变异、差异、内在蜕变的欲望越多,那里就越有力量。
在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里,相互接近的本能——与拒斥某物的本能,
乃是一个纽带。全部区分都是一种偏见。
在任何力量组合中的权力意志,在反抗强者,冲向弱者之际,
是真正的权力意志。注意:作为“本质”(Wesen)的过程。
36[23]
持续不断的过渡不允许我们谈论“个体”(Individuum)等等;
存在物的“数”本身在流变中。倘若我们不相信自己以粗略方式看到了与运动之物并存的静止之物,
那么,我们或许就不能谈论时间,对运动一无所知。对于原因与结果也一样,
要是没有关于“空洞空间”的错误构想,我们根本不会有关于空间的构想。
同一律的背景乃是“亲眼目睹的表面现象”(Augenschein),
即认为存在着相同的物。一个生成的世界或许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被把握”的,
是不能“被认识”的:
唯就“进行把握”和“进行认识”的理智找到了一个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粗糙世界,
一个根据完全的表面性造出来的、但已经变得固定的世界,
只要这样一种假象把生命保存下来——唯就此而言,才有某种诸如“认识”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更早的和更新的谬误之间的相互比较和衡量。
36[30]
当人们说笛卡尔诉诸上帝之可信性是轻率之举的时候,人们不合理地反对了笛卡尔。
实际上,只有在假定一个在道德上对我们来说同质的上帝的情况下,
“真理”以及对真理的寻求才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成果可望和具有意义的东西。
撇开这个上帝,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受骗上当是不是生活的条件之一?
36[31]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力”这个常胜概念创造了上帝和世界。这个概念还需要有一个补充:
必须把一个内在的世界判给这个概念,我把它称为“权力意志”,
也即对权力之显示的永不餍足的要求;或者说对权力的运用、实施,
作为创造性的欲望等等。物理学家不能摆脱自己原则中的“远距效应”:
同样也无以摆脱一种排斥力(或者吸引力)。这些毫无助益:人们必须把一切运动、
一切“现象”、一切“定律”都仅仅理解为一种内在事件的征兆,最终要动用人类的类比。
从权力意志中衍生出欲望,这在动物身上是可能的:
同样,有机生命的一切机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1885年6月至7月
37[8]
无可拒绝、迟疑、可怕如同命运,一个伟大的使命和问题临近了:应当如何来掌管作为整体的地球?
还有,应当为何来培育和教育作为整体的“人类”——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
立法的道德乃是一个主要手段,靠着它,
人们可以从人类身上塑造出一种创造性的和深度的意志所欢迎的东西,其前提是:
这样一种最高等级的艺术家意志手上掌握了暴力,能够以立法、宗教和伦理为形态,
长时期地贯彻它的创造性意志。这样一种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人类,这种真正伟大的人类,
以我的理解,在今天很可能是人们还长期无法追随的,因为他们付诸阙如;
直到最后,在经历了种种失望之后,人们一定会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付诸阙如,
他们的出现和发育,除了现在在欧洲径直被命名为“道德”的东西之外,
在今天以及长期地都没有任何更具敌意的东西挡在路上:仿佛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其他道德了
——就是我们刚刚描绘过的群盲道德,后者竭尽全力追求地球上普遍的、绿色的牧场幸福,
也即生活的安全、无危险、舒适、轻松,终于,“如果一切顺利”,
就希望自己也还能摆脱一切种类的牧人和带头羊。他们的两个最多地被传布的学说叫做:
“权利平等”与“同甘共苦”——而且苦难本身被他们当作某种绝对必须废除掉的东西。
这样的“理念”始终还可能成为时髦,这一点给出一个令人厌恶的关于——的概念。
但谁若彻底地思考了,迄今为止人这种植物在哪里以及如何得到了最有力的生长,
他就必定会以为,这是在相反的条件下发生的:此外,人的处境的危险性急剧增长,
人的发明力和伪装力在长期的压力和强制下顽强抗争,
人的生命意志必须被提升为一种无条件的权力意志和强大优势,危险、冷酷、暴力、
胡同里(如同心脏里)的危险、权利不平等、隐蔽、斯多亚主义、引诱者艺术、
任何暴虐行径,质言之就是一切群盲愿望的对立面,都必然地要提高人这个类型。
一种带有此等相反意图的道德(它要培育人,使人提高而不是使人进入舒适和平庸状态),
一种意在培育统治阶层的道德——未来的地球主人37[8]
无可拒绝、迟疑、可怕如同命运,一个伟大的使命和问题临近了:
应当如何来掌管作为整体的地球?还有,应当为何来培育和教育作为整体的“人类”
——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
立法的道德乃是一个主要手段,靠着它,
人们可以从人类身上塑造出一种创造性的和深度的意志所欢迎的东西,其前提是:
这样一种最高等级的艺术家意志手上掌握了暴力,能够以立法、宗教和伦理为形态,
长时期地贯彻它的创造性意志。这样一种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人类,这种真正伟大的人类,
以我的理解,在今天很可能是人们还长期无法追随的,因为他们付诸阙如;
直到最后,在经历了种种失望之后,人们一定会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付诸阙如,
他们的出现和发育,除了现在在欧洲径直被命名为“道德”的东西之外,
在今天以及长期地都没有任何更具敌意的东西挡在路上:仿佛不存在、
也不允许存在其他道德了——就是我们刚刚描绘过的群盲道德,后者竭尽全力追求地球上普遍的、
绿色的牧场幸福,也即生活的安全、无危险、舒适、轻松,终于,“如果一切顺利”,
就希望自己也还能摆脱一切种类的牧人和带头羊。他们的两个最多地被传布的学说叫做:
“权利平等”与“同甘共苦”——而且苦难本身被他们当作某种绝对必须废除掉的东西。
这样的“理念”始终还可能成为时髦,这一点给出一个令人厌恶的关于——的概念。
但谁若彻底地思考了,迄今为止人这种植物在哪里以及如何得到了最有力的生长,
他就必定会以为,这是在相反的条件下发生的:此外,人的处境的危险性急剧增长,
人的发明力和伪装力在长期的压力和强制下顽强抗争,
人的生命意志必须被提升为一种无条件的权力意志和强大优势,危险、冷酷、暴力、
胡同里(如同心脏里)的危险、权利不平等、隐蔽、斯多亚主义、引诱者艺术、
任何暴虐行径,质言之就是一切群盲愿望的对立面,都必然地要提高人这个类型。
一种带有此等相反意图的道德(它要培育人,使人提高而不是使人进入舒适和平庸状态),
一种意在培育统治阶层的道德——未来的地球主人——,为了能够得到传授,
就必须把自己引入与现存伦理准则的联系之中,并且隶属于现存伦理准则的话语和假象;
但为此必须发明出许多过渡手段和欺骗手段,还有,因为着眼于如此漫长的使命和意图的实现,
一个人的寿命几乎无关紧要,所以首先必须培育一个新的种类,在其中,
许多世代保证了同一种意志、同一种本能的延续:一个新的主人种类和主人阶层——
后者同样很好地把自己理解为这种思想的漫长的和不易表达的“如此等等”(Und-so-weiter)。
为某个特定的具有最高精神性和意志力的人的强大种类准备一种价值颠倒,
为此目的,慢慢地和小心地把他们身上大量被羁绊和被诽谤的本能释放出来:
谁来思考这一点,他就属于我们行列,属于“自由精神”——
当然可能属于比以往更新的“自由精神”种类:因为以往的“自由精神”想望的差不多是相反的东西。
在我看来,后者主要包括欧洲悲观主义者,一种愤怒的唯心主义的诗人和思想家们,
因为他们对总体此在的不满至少在逻辑上迫使他们也不满于当代人;
同样还有某些贪婪的和虚荣的艺术家,他们毫不迟疑地和无条件地反对“群盲”,
为高等人的特殊权利而斗争,并且用挑选出来的人物那里的艺术的引诱手段来麻醉
所有群盲之本能和群盲之谨慎;最后第三部分,就是所有那些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他们大胆地继续推进幸运地开始的对旧世界的发现——新的哥伦布的作品、
德国精神的作品(——因为我们始终还处于这种征服的开端中)。
因为在旧世界中,占上风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今日的道德,一种更华丽的道德;
古代人,为其道德教育魔力所吸引,是一种比今日人类更强大和更深刻的人,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发育完好的人”。但那种引诱,那种从古代出发施加给发育完好的、
也即强壮的和行动的心灵的引诱,即便在今天也还是所有反民主的和反基督教的引诱中
最精致的和最有效的一种:正如它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那样。
1885年6月至7月
38[13]
我年轻时曾忧心于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一个哲学家是什么。
因为我当时以为自己领会到了与那些著名哲学家相对立的特征。
最后我明白了,存在着两个不同种类的哲学家,第一类哲学家必须以某种方式抓住大量的价值评估,
也即从前的价值评估和价值创造(逻辑的或者道德的),
而第二类哲学家本身就是价值评估的立法者。前者力求掌握现成的或者过去的世界,
其做法是通过符号来概括和简化这个世界。
这些研究者致力于把所有以往发生的事和以往所做的评估搞成可综观的、可思考的、
可把握的、便于使用的,致力于征服过去,把一切久长的东西实即时间本身缩减——
委实是一项伟大而神奇的任务。然而,真正的哲学家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
理当如此!他们首先规定人类的何往和何为,同时支配着那些哲学工作者
(那些征服过去的人)的准备工作。这第二类哲学家天生稀罕;而且实际上,
他们的处境和危险是阴森可怕的。他们多么经常地有意紧闭自己的眼睛,
只为了不必看到那种把他们与深渊和悬崖分离开来的细微边缘:例如柏拉图,
当他说服自己相信他要的善并不是他柏拉图的善,而是善本身,是永恒的珍宝,
只不过一个叫柏拉图的人在路上找到了它!这同一种盲目意志以粗糙得多的形式
在那些宗教创始人那里起支配作用:他们的“你应当”(du sollst)
在他们的耳朵听起来完全不像“我要”(ich will),
——只是他们胆敢把遵守上帝的命令当作自己的使命,只是作为“灵感”(Eingebung),
他们的价值立法乃是一种忍受得了的、使他们的良心不至于破灭的重负。
——一旦柏拉图和穆罕穆德,已经失效,再也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靠“上帝”或者“永恒价值”的
假设来缓解自己的良心,则新价值之立法者的要求就上升到一种新的、尚未达到的恐怖状态。
现在,那些特选民(在他们面前,关于这样一种义务的猜度开始变得明朗了)将做出试验,
是否他们想通过某种荒唐行为还“适时地”从这种义务中溜走(仿佛把它当作自己的最大的危险):
例如他们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任务已经解决,或者任务是不可解决的,
或者他们负担不起这等重负,或者他们已经负担了其他更进一步的任务,
或者连这种新的遥远的义务也是一种引诱和诱惑,一种对全部义务的拒绝,
一种疾病,一种疯狂。实际上可能有些人已经成功地逃避:贯穿整个历史,
布满了此类逃避者及其坏良心的痕迹。但这种厄运之人多半会获得那拯救时刻,
那成熟的秋季时分,当其时也,他们一定会得到他们都不敢“想望”的东西:
——而他们向来多半惧怕的行为,轻易而无意地从树上掉落到他们身上,
作为一种毫不任性的行动,几乎作为赠礼。1885年8月至9月
39[17]
人们可以希望人变得如此崇高,以往至高之物,例如以往的上帝信仰,
在人看来都显得那么幼稚可笑,那么动人,是的,人有对待所有神话的办法,
再一次做了这事,也就是把〈以往至高之物〉转变为儿童故事和童话了。
40[32]
假如你们问:“五万年前树就是绿色的吗?”我会说:“也许还不是绿色的:
也许当时只有两种主要色调的对立,即明与暗的对立:——渐渐地,从中展开出种种颜色。”
40[39]
物理学家现在与所有的形而上学家达成了一致,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幻觉和欺骗的世界里:
幸运的是,人们不再需要用某个上帝来清算这一点了,
人们可以奇奇怪怪地思考上帝的“真诚性”了。世界的透视性质已经深入人心,
超过了今天我们的世界“理解”所能达到的;而且我会冒险一试,
仍旧在人可以正当地撇开理解的地方开始——我指的是那个地方,
形而上学家在那里〈开始规定〉表面上自身确定、自身理解的东西的领域,
也〈即〉在思维中。数字是一种透视形式,恰如时间和空间,
我们既不会把“一个心灵”也不会把“两个心灵”藏在胸内,
“个体”就像物质“原子”一样不再能保持下来(除了为思维的日常使用和私人使用),
而且已经悄悄溜入虚无中了(或者溜入“公式”中),任何生者和死者都不能加在一起,
两个概念是虚假的,不存在第三种心灵能力,“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
“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始终只不过是透视形式,总而言之,心灵、实体、数、
时间、空间、根据、目的,——它们存亡与共,彼此共兴衰。但假如我们并非如此愚蠢,
去高估作为假象的真理(在此情形中即X),假如我们下定决心去生活——
那么我们就不会满足于这种事物的虚假性,而且只会坚持认为,
对于无论何种隐含思想(Hintergedanken),没有人会停留于这样一种透视性的描绘中:
——这实际上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哲学家遭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有所有的隐含思想,
热爱他们的“真理”——可是,我们在此必须提出关于真诚性的问题:
假如我们生活在谬误序列中,那么,在此“求真理的意志”可能是什么呢?
难道它不是必定会成为一种“求死亡的意志”么?——哲学家和科学人的努力也许就是蜕化的、
垂死的生命的一个征兆,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生命—厌烦(Lebens-Überdruß)?
Quaeritur[有人问]:在这里,人们或许真的会变得深思熟虑。
40[49]
我们要怀疑所有表面的“同时性”!这里插入了时间碎块,它们只按照一种粗糙的尺度,
譬如按照我们人类的时间尺度,才可以被叫做小的碎块;而在异常情况下,
例如作为吸大麻者或者在有生命危险的瞬间,我们人也获得了一个概念,
知道我们怀表上的每一刻都可能想出无数个思想,经历无数个体验。
当我睁开眼睛时,可见世界已然在此矗立,看来是立即出现的:
但在此间,某种惊人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多种多样的事件:——第一、第二、第三:
不过在这里,生〈理学家〉有话要说!
40[59]“相互交往的人”的结尾前言与预备问题“什么是自由精神?”
〈1〉
“一个蕴含世界智慧的心灵,必须通过自己的健康而同样地使身体健康”,蒙田如是说。
今天作为一个在此领域里富有经验的人,我乐于赞同蒙田的话。
“没有比世界和世界智慧更活泼、更伶俐——我差不多想说——更娱乐的东西了”,
我同样随着蒙田如是说。——但在当时,智慧是以何种苍白而可怕的面具与我交臂而过啊!
够了,我时常对智慧心存恐惧,不愿如此与智慧独处——并且开始了向南方漫游,
孤独而沉默寡言,但却带着一种顽强的“求智慧的意志”。当时我把自己称为“自由精神”,
或者“自由鸟王子”,谁若问我你到底家在哪儿呀,我就会回答他:“也许在善恶的彼岸,
不然就没什么地方了”。但我如此艰难地独自承受,没有一个同道:于是有一天,
我向其他的“自由精神”抛出了一个钓钩——连同这本书,
我已经把它命名为“一本为自由精神的书”。
然而时至今日——十年间人们不能学会的都是什么呀!——我几乎依然不知道,
我是否用这本书在寻求同志和“同道”。因为此间我学会了承受孤独、
“领会”孤独(这是现在少有人懂的):而且,如今我会直接认为“自由精神”的本质标志在于,
他喜欢独自奔跑,喜欢独自飞翔,甚至于如果他的腿有病,他便喜欢独自爬行。
孤独若不能治疗,便是致命的:这是真的;孤独乃是一种糟糕的和危险的治疗术。
但确凿无疑地,如果孤独能治疗,它也就能把人置于更加健康和更加自负的境地,
胜过社会中的一个人、森林里的一棵树向来可能有的情况。
孤独最彻底地考验(超过无论何种疾病本身),一个人天生或命定要活下去,
抑或像大多数人一样死掉。好了,我只是从孤独中学会了完全彻底地
思考“自由精神”与“健康”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
2
我们这些“自由精神”独自生活在地球的某个地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
我们是少数——这也算公道罢。我们骄傲地认为,我们这个种类是一个稀罕的和奇特的种类;
我们并不相互排挤,也许都没有相互“怀念”。当然啰,若像今天这样相聚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节日了!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哲学意义上来使用“幸福”一词,那么,
我们是不会像哲学家当中的厌倦者、恐惧者、受苦者那样,首先想到内部和外部的和平,
想到无痛苦、不受感动、不受扰乱的状态,想到“安息日中的安息日”,
想到可能接近于价值中的沉睡的某种东西。而毋宁说,我们的世界是不确定的、
变化多端的、意义模糊的,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无疑更超过了那种简单的、
自身相同的、可计算的、固定的东西——迄今为止,
哲学家们都把后者当作群畜本能和群畜估价的遗产,给予了一种至高的荣耀。
在许多精神国度里得到承认,到处流浪,如此等等。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