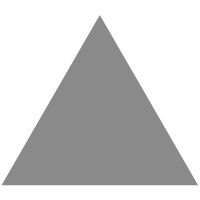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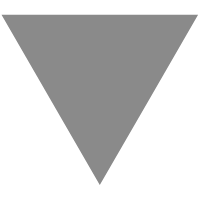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赵建:降准的政治经济学——谁能决定水流的方向
source link: https://www.gelonghui.com/p/474348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赵建:降准的政治经济学——谁能决定水流的方向
10分钟前
1,441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西泽研究院,作者:赵建
降准了,水会流向哪里?
树长不到天上,水也只能向低处流。当经济进化到无比复杂的现代经济体,当货币深化到无比精致的现代金融体系,宏观管理的理念和工具进化了多少?
比如,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比例,现代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比如,定向降准这一为了维护政策“道德”而有违货币自由本性的无奈手段。
如果货币是中性的,那么所有依靠货币刺激的增长都只是一个幻觉。只是因为,货币滥发的社会成本还没显现,它们可以在不同代际之间转移。如果货币扩张的时滞可以长时间延迟,那么货币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场信用资源的代际取舍——我们这一代还能给下一代留下多少宽松空间?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信用生态?是互相信任还是互相伤害?
眼前,从货币到信用之间,从基础货币到广义货币之间,似乎越来越远。这一次降准,首先是帮助中小银行同业救急,其次是支持上半年过于激进的财政融资。至于中小民企,无论是信贷可得性还是低成本融资,都还需要遥远的传导和漫长的时滞。
问题的关键,很显然是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关键又是“商业”二字。如果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能或者只会做财政出纳和土地银行,那么所有的降准降息释放的货币,都只能继续淤积在这两大“行业”。路径依赖下,一切都只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当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银行家精神。货币与信用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缺乏的恰恰是真正的银行家精神。此时此刻,它与企业家精神一样稀缺。
货币是现代经济的“活水”。上善若水,此处的“善”不是道德的审判,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经济之道,道法自然。从存贷基准到LPR,从法定存准到MLF,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的表现。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比利率市场化更重要,或者说与其同等重要的是,银行的再商业化。
只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真正的按照商业和市场的逻辑配置资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才会真正疏通,降准降息释放的“活水”才会通过商业银行专业的风险作业模式流向实体经济。否则,仍然是流入财政和房地产这两大水池,透支本属于未来的信用,制造泡沫、通胀和两极分化的“祸水”。
一、理解货币政策的中国特色:转轨经济体的货币控制
观察和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西方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当前依然处于转轨过程中,所谓的深化改革。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我们暂且定义为当前中国处于后转轨时代。
转轨经济体属于发展经济学或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内涵和外延都比较丰富。单单从货币政策的领域来看,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货币深化与货币控制长期并存,或者是沿袭了传统的改革技术——双轨制。
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转轨国家的货币政策拥有的手段和工具更加强大。仅举几个:
1.存贷款利率管制。这基本相当于计划经济模式,同水电煤气等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类似的价格控制。它们都是镶嵌在市场经济中的计划领地。虽然利率市场化名义上完全放开,但为了避免打价格战,央行依然保留”窗口指导“的权力。即使现在新定义的lpr,实际上也是市场和计划的混合体。
2.金融企业的牌照。被政府严格的控制,申请此类企业的牌照不仅简单的看经济意义上的审查,还要看”身份“和”出身“。
3.金融企业的产权。几乎百分之九十的直接或者间接国有(包括地方国有)。这直接决定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以及传导到的经营偏好,包括客户偏好(国企和政府)、风险偏好、人才偏好(关系型人才)、管理偏好(层级权威、官僚主义)。
4.监管部门的干预。从客户选择到定价权,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银行可自主经营的空间越来越窄。监管和经营机构之间最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旋转门”现象,到金融机构任职的监管官员越来越多,也说明他们早就熟悉了金融机构的管理细节。
5.央行的信贷额度。所谓的“合意贷款”,几乎等价于计划经济配额管理。
6.各种各样的“窗口指导”。这个可能比固定规则的计划管制更严重,因为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有时候都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让经营单位无所适从。
7.外汇管理中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属于强制性的将外汇资产国有化,但保留着一部分购汇的权力(个人每年5万美元)。
这种强大的金融控制力,对于转轨经济体至关重要:一方面是保证转轨经济体稳定转型的保障,毕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之重器,有多少转型国家倒在了金融自由化过快的泥潭中;另一方面,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强有力、更多选择的工具和手段。
比如,与美联储等金融已经市场化的国家央行相比,中国央行竟然可以直接管理到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行业投向和定价基准。甚至,可以改变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直接任命高管或者增加治理主体(党委会)。这些在发达金融国家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我们的防风险攻坚战和金融去杠杆,才会发挥出举国体制的“效果”。
聚焦到本文的主题——降低存款准备金,以及接下来的降息,我们也应该在中国转轨经济体的特有背景和中国央行特别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首先,中国央行的世界高水位的存准是怎么形成的?这里面有一个漫长而又深刻的历史逻辑——外汇储备的周期,从快速上升期(2000s),到峰值(2014),再到下降期。这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而在其负债端,也就主要对应着存准的变化,主要是法定存准的变化。
问题是,2014年当外汇储备进入下降阶段后,央妈为了不缩表以保持基础货币供应的稳定性,开始大面积采用一系列“公开市场工具”,比如MLF、SLF等,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有条件的“再贷款”。这就出现了我以前常说的转轨经济体在金融管制上的一个悖论:
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较高的利息成本从央行借MLF等,另一方面,大量被限制的流动性又被锁在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商业银行辛辛苦苦“拉来”的存款(总体上看是贷款派生的,但单个银行尤其是小银行却是各种营销来的),最高时要五分之一上缴央行。严格来说,被锁住的法定存准才是真正的“资金空转”,它相当于强制让商业银行配置低收益的央行债务。
所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角度,从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交易关系”角度理解降准,不过是将人为管制的流动性或基础货币释放出来。体现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从法定存准转移到超额存准的科目变换。如果没有信用的创造,并不一定意味着广义货币总量必须扩张,因为货币乘数并不一定会提高;或者即使货币乘数提高了,但基础货币不一定提高,这涉及到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机理。
二、货币的自由本性与定向管制型降准的悖论:降准能增加广义货币吗
虽然,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需要转轨国家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基本的货币银行学原理却不能超越。再特殊的树,也不可能长到天上;再不一样的水,也不可能流向高处。特色的,也是普世的。只不过,特色只是暂时超越的幻觉。哲学思辨,一和多,形式和实质。
我不想谈货币哲学,但或许可以谈谈货币“伦理学”。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披上了公共道德的外衣,似乎一降准降息就是“放水”,就是罪恶滔天。货币政策被妖魔化,是货币金融体系不成熟的表现。货币当局当然要管理社会预期,但没有必要如此言不由衷、缺乏自信。道理讲明白,传播出金融理性,尊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自然就不会有大的预期冲击。毕竟,美联储都直接“直升机撒钱”了。
大国经济,比大国经济更大的是大国金融。总量已经是毫无疑问的超级规模:广义货币的存量,金融业的增加值,都已经天下第一,前者已经超过美欧总和;世界五百强有多少家是中国的银行,金融上市企业的利润早就占据半壁江山,金融企业的纳税和上缴利润也是独占鳌头。但世界第一的金融产能却服务不了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不了新兴科技和新动能产业,逼得央行创新出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型降准。基本的原理不过是想将宽松释放的流动性流向政策层想要的领域。
然而货币是自由的,在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下,货币选择的地方只有一个:利润洼地,也就是赚钱的地方,或悲观时避险的地方。即使你强制的改道或者堵塞别的管道,也会有各种通道或嵌套结构绕道流淌。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商业的智慧也无穷。比如前段时间对中小企业的定向降准或者低息贷款,就有不少银行和企业合作,或者修改企业的口径符合降准要求,或者找个符合标准的小企业作为通道或者干脆新注册个企业,以套取低息定向贷款。最终的“水”流向哪里了呢?无外乎一是通过结构化绕道依然趴在银行账户上(票据—结构化存款),二是依然流向了平台和房地产。
这是个逻辑上和现实中都可以验证的问题,或者说“政策的定向意志与货币的自由本性”之间的悖论。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关系。降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稳定经济,直接目标或者中介目标是创造货币,创造广义货币,也就是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中国经济要保卫“3、4、5、6、7、8、9、10”,其中的“8”就是广义货币的增速,最新的数据是7月份,同比增长仅有8.1%。非常严峻的数据。
然而实际上,就连这8%的同比增速,也包含了不少“水分”。因为在统计口径里,包括了不少的非银存款,而非银存款前几个月也新增了不少,维系了广义货币的增速没有严重塌缩,目的可能是为了管理好社会预期和公共信心。那么降准能否达到保卫广义货币增速“8”的目标呢?可能要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或者放弃总量的速度,或者放弃结构的定向。也就是,如果坚持不放松在信用上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的总量控制,而坚持定向支持民企和中小微,那么广义货币增速的继续下滑剔除短期扰动后几乎难以避免。因为当前能够相对较快的创造信用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平台(政府信用),选择放松对它们的管制,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毫无疑问会继续涌向这两大领域。当前的形势来看,中央政府似乎下了决心“去房地产化”,捏住了房地产融资的“七寸”——信托贷款(单一信托和集合信托都开始限制),并且禁止对按揭贷款下调利率,几乎堵塞了所有流向房地产的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定向降准会增加广义货币创造的动力吗?我们知道“广义货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降准一定会提高货币乘数吗?不一定,因为货币乘数的分母是总的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法定存准降低了但银行依然缺乏放贷的动力,那么这些改变“账户科目“的法定存准不过是转为了超储,总的存准率不变。或者,存准率降低,但是因为银行可支配的头寸多了减少了对央行的MLF和OMO交易等,基础货币将会减少(对应着央行缩表),那么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相乘也不一定提高。
这不过是公式数字的”形而上“推演,现实中广义货币的创造来自于实体经济的信用,也就是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而这,一方面的确受制于经济的内生性收缩,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风险管理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
三、降准有效传导的关键:商业银行“再商业化”与广义货币的“再深化”
中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中国整体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同步,但由于银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产业,改革的步伐和节奏略微缓慢。但不论怎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中国的商业银行不断进行公司化和市场化改革,持续提升“商业化”程度,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也就是所谓的初心。
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专营,九十年代的公司化,还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资本市场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的商业和专业程度都在不断提升。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后,陷入出口依赖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巨大的通缩压力,中国商业银行开始承担起“反危机”的政策性银行功能。四万亿首先是强制性的贷给民企,但很快就爆发了以钢贸和过剩产能行业为主的信用危机。此后,新一轮信用周期,银行开始通过影子银行一窝蜂的做政府平台和地产金融。整个信用体系虽然在总量上膨胀,但结构上却在通缩,即带有政府刚兑或准政府刚兑的信用在膨胀,但民企和小微企业的信用却在收缩。其实这本质上并不是金融或银行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执行信贷政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快。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利率管制逐渐放开,市场化的银行理财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大资管”和“泛投行”快速繁荣,直到金融严监管后的信用收缩。虽然金融市场化在明显加快,但是存款准备金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位,其中有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下央行管理流动性的要求,不过对法定存准的限制,本质上也是一种较强的管制手段。当前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存款准备金已经很少作为常规性工具,因为普遍的“流动性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降准是中央银行将货币经营的自主权放权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在商业规则的约束激励下,将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支持贷款给产业资本,最终顺畅的支持实体经济。道理很简单,不过是常识的回归,没有必要加那么多定语。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膨胀不一定是好事,那是经济危机来临后不得不量化宽松造成的后果,以至于到最后缩表瘦身成为不可能。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流动性是不可逆的,所谓“覆水难收”。
可见,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央行的货币政策也需要随之重塑基本框架,更多的应该采用经济和市场的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和计划安排。所以从金融市场化的角度来看,的确应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而换之以各种公开市场工具。从“外汇资产——法定存准”到“MLFs——超额存准”,可以看作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过程。
对于降准,从基础货币释放到实体经济信用扩张,中间的关键依然是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继而客户偏好的改变。为了拯救衰退的信用,打通央行与实体经济的管道,我们需要一个商业银行“再商业化”的过程,以及伴随的广义货币“再深化”的过程:
首先是公司治理方面,真正的采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说到底,公司治理体制是一个银行的“政治体制”,业务体制是“经济体制”。如果银行是追求利润或者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规模和地位升迁,那么只要能赚钱,就会提高风险偏好支持民企和中小微。新时代,党委的作用很重要。对商业银行来说,商业银行不是一般的企业,是经营风险的带有外部性的金融机构,党委会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但是治理范围要有边界,不能随意干预自主经营。技术性工种党建化是造成专业能力缺少的原因之一,也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其次是完善监管机制,说到底就是重新划分好监管和银行的边界。最近几年商业银行对民企和小微企业的抽贷断贷,虽然有经济周期的原因,但严厉的金融去杠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量减少一些运动式监管,多一些固定的规则,不能今天合规的事情明天突然被认定不合规。如果政策风险较大,为了避险,银行就会找政治正确而不是风险收益率高的客户,比如国企和地方平台,因为都是体制内,风险不会扩大化。
第三,切实推进利率市场化,两轨并一轨要尽快完成,不要搞名义和实际两层皮,滥用窗口指导。否则,平台和房地产以及国企,会继续利用体制性信用利差进行套利,严重损耗这个系统的效率,在快速的做大规模(理论上可以无穷大)的同时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第四,要逐步但是坚决打破刚兑,打破银行的“金饭碗”;有序推进银行业的兼并重组,让银行从不良压身的“僵尸模式”走出来,轻装上阵服务实体经济。但无论如何,高质量发展模式不需要这么多的低效金融产能,应该加快市场出清,减少金融和流动性资源的无谓消耗。
第五,培养真正的银行家精神。笔者从事过银行工作近十年,发现这十年随着老一代银行董事长、行长的退休,银行家精神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上两代银行家更注重战略和创新,那么新一代银行领导人关心的更多的是合规和稳健,以及更大范畴的政治正确。倒不能说是中国银行家精神的退化,应该说是新时代银行家精神有不同的内涵。
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追责问责机制的改变,真正做到“尽职免责”,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比如金融科技在银行经营机制中的应用,将原来无法形成信用的数据形成信号和信任,最后通过算法形成信用,等等 。
总之,殊途同归,回到常识,降准的活水要流到实体经济,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好的体制环境—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而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也不仅仅是基准利率的名义放开,而是真正实现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本质。这不过是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要求,如今来看恰恰是真正的“不忘初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降准的货币政策才能真正提振实体经济和广义货币的创造,央行释放的“活水”才会流向需要的地方。所谓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本文原发表于2019年9月。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