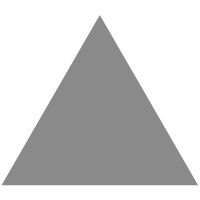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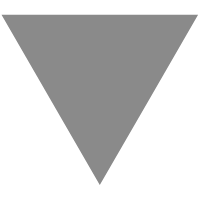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万字长文揭秘谷歌成长史:荒诞梦想的副产品
source link: https://tech.sina.com.cn/i/2018-07-17/doc-ihfkffak9603782.shtml?amp%3Butm_medium=referral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导语:
科技专栏作家亚当·费希尔(Adam Fisher)写的《硅谷天才》(Valley of Genius: The Uncensored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近日出版,里面描述了硅谷各家主要科技公司的创业史,其中包括 谷歌 早期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篇口述历史结合第一手资料和之前发布或未发布的回顾,讲述了谷歌走下神坛的历程,以及又如何在觉醒中改变了一切。
互联网上最具影响力公司的幕后描述——从研究生的通宵学习、太空缆索和“火人节”到“矩阵的特殊矢量”,再到这家公司的巨大财富和无穷力量。
 拉里·佩奇(左),谢尔盖·布林,在谷歌山景城园区的服务器室内,2003年。
拉里·佩奇(左),谢尔盖·布林,在谷歌山景城园区的服务器室内,2003年。
1996年,随着万维网的兴起,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仍在场外观望。和硅谷的其他人不同,他们对使用互联网购买、出售物品,或者阅读和发布故事,甚至获得感恩至死乐团的门票均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着用互联网来获得自己的博士学位。网络是计算机科学的未知前沿,而佩奇和布林对网络内容可以说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了解网络的样子。
因此,就其资本主义化身而言,谷歌算得上是一个意外——毕业生的奇思妙想、好奇和荒谬梦想的一个偶然副产品。公司几乎完全建立在“火人节”(火人节节庆是一年一度在美国内华达州 黑石 沙漠举办的活动,被许多参与者描述为是对社区意识,艺术,激进的自我表达,以及彻底自力更生的实验)之上,因为谷歌的真正目的向来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打造自动驾驶汽车,开发可以进入外太空的电梯,甚至有一天(这一天似乎正快速向我们接近)实现真正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佩奇、布林和斯科特·哈桑——不为人知的谷歌“第三位联合创始人”——正在建造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把我们浏览互联网的时间转变成金钱。金钱只是这个伟大计划的第一步。早早退出谷歌的哈桑仍在寻找长生不老之道,仍在探索如何殖民太阳系。佩奇和布林留了下来,跟着谷歌一道成长、变现、并彻底文明化。“这真的很令人沮丧。”一位早期员工说。
第一部分:“统治世界”
大卫·切瑞顿(David Cheriton,斯坦福大学教授兼谷歌的种子投资人):大概是在1994年或者1995年,我记得谢尔盖正在计算机科学大楼的四楼附近跟我的几个研究生滑旱冰。
斯科特·哈桑(Scott Hassan,计算机科学部门的程序员):谢尔盖和我是好友,我们会四处溜达看看有没有撬锁的机会或者干些别的事情。我们可以打开整个地方的任何一扇门!
希瑟·凯恩斯(Heather Carins,斯坦德大学管理员,后来成为谷歌第四号员工):谢尔盖会带着糟糕的绘画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学过艺术,然后询问我的意见。那些画很抽象,大概就是棕色背景上的黑色涂鸦而已。他可能是想模仿罗斯科或者其他人,谁知道他呢。我告诉他,别老不务正业了。但话说回来,你真得佩服他的这股劲。谢尔盖有点喜欢到处炫耀自己,绝对是一个外向的孩子。
哈桑:然后到了第二年,拉里以博士新生的身份出现了。拉里非常与众不同。
凯恩斯:拉里是个内向的人。
拉里·佩奇(Larry Page,谷歌联合创始人):1995年我还是个博士生的时候,我就对自动化汽车十分感兴趣。我脑子里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大概有10多个。
凯恩斯:建造太空缆索把人送进太空也是一大雄心壮志。
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佩奇的论文指导):嗯,所谓太空缆索的基本想法就是扔一块石头到太空里,放在轨道上沿着地球转,下面连一根直通到地上的绳子,其实就是一个电梯。有点像童话故事《杰克与豌豆》里讲的那样,你懂的。
凯恩斯:啊,没错,太空缆索。那时候,他们还在讨论这玩意。我从没想过这主意是认真的,不过显然他们是认真的。
威诺格拉德:他们就是单纯的喜欢思索。“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造一个太空缆索呢?建造太空缆索需要些什么呢?”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谷歌联合创始人):我对数据挖掘很感兴趣,所谓数据挖掘就是分析大量数据,发现其中的模式和趋势。同时,拉里开始下载网络,然而我发现,那可能是你可以挖掘的最有趣数据。
佩奇:23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某一天我突然醒来时,就在想,要是我们可以下载整个网络,然后保存那些链接的话……
哈桑:……反向浏览网络!主要是它听上去真的很有意思。你可以说,“哦,我在这个页面上,哪个页面指向我?”对不对?所以,拉里想要开发一种方式反向查看谁链接到谁。他反向浏览整个网络……所以拉里接下来就开始写了一个网络爬虫。那个网络爬虫干的事情就是:你给它一个起始页面,然后它开始下载这个页面,下载完之后浏览这个页面找出其中所有的超链接,继而在下载超链接的页面,继续重复前面的步骤,这就是拉里写的网络爬虫。
威诺格拉德:获取数十万个页面然后下载它们可是个大工程。
哈桑:95年秋天,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开始和拉里在他的办公室打发时间……当时,拉里正想法子怎么同时下载数百个页面。我就帮他修补他写的Java脚本里的一些漏洞,就这样我们忙活了大约几周的时间,也可能是几个月。我记得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天呐,这太疯狂了!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修复这个底层工具。所以在一个周末,我拿走了他的所有代码,拿走了他的所有内容,然后全部扔干净,接着我迅速重新写了一遍他这几个月来一直忙活的东西。大概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吧,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修补Java的漏洞了。我知道,如果我使用一种我更为熟悉的语言——也就是Python,来工作的话,效率会高很多。然后,我让我的代码可以同时下载3.2万个页面。这样,拉里就可以在一台机器上从勉强下载100个页面飞跃到同时下载3.2万页面。
威诺格拉德:斯科特是个程序员。我不知道内情,但据我所知,根据拉里说的话,基本的情况就是“好吧,我们需要一个代码可以做这和那的”,然后斯科特转身就开始写代码了。
哈桑:周一的时候我兴冲冲地向拉里展示我的杰作。但是拉里扫了一眼然后说,“很好,但是好像这里有个问题,那里也有个问题……”他立即指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很快,又变成了他告诉哪里不对,然后我又得修复这些问题——要知道我费劲重写个代码就是为了避免不断修复问题这个麻烦事。
佩奇:令人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开发一个搜索引擎。压根连边都没着过。
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纽约时报”驻硅谷记者):当时有很多的搜索引擎,可以说到处都是。写一个爬虫然后下载网络并非谷歌的突破。PageRank才是。
威诺格拉德:我记得拉里说起过在网络上随机漫步。“自由冲浪”,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在某一个页面上,身处于浩瀚的网络中,这个页面上有一堆链接。你随机选择一个链接点开。然后,你用大量机器人不断重复这个动作。那么,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最后会怎样呢?关键是,如果很多人指向我的话,你会有更多可能到达我这里。我很重要——所以我可以获得大量流量。再接着,如果我指向你,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大量流量,哪怕从我指向你的链接只有一个:因为我有巨大流量,所以你也可以获得巨大流量。试想一下网络上的这种流量移动方式,仅考虑数据统计。谁会获得最多的流量呢?
哈桑:拉里找到我,说了他的随机漫步的想法,但是拉里不知道如何计算它。谢尔盖看了看,说:“啊哈!这看起来跟计算矩阵的特征向量很相似啊!”
布林:基本上就是,我们把整个网络变成一个巨大的等式,里面有几亿个变量,它们是所有网页的页面排名,还有几十亿个术语——也就是链接。然后,我们可以解决这个等式。
佩奇:然后我们就说,“天啊,这太棒了。它可以照着你期望的顺序进行排序!”
布林:接着我们写了一个叫BackRub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非常原始,它其实仅读取了网页的标题,但在生成相关搜索结果方面,它已经比当时已有的搜索引擎好很多了。比如,如果你搜索斯坦福的话,你可以在结果中找到斯坦福的主页。
哈桑:然后我找来所有人,说,“各位,我们不如开发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吧!”挺好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拉里和谢尔盖都觉得工程量会很大。我就说,“不不不,其实没那么多工作。我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巴特勒·兰普森(Bulter Lampson,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一个搜索引擎由两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爬取整个网络然后搜集所有页面,另一个部分就是给这些页面建立索引。当然,如今的搜索引擎还有第三部分,处理相关部分。它必须知道对于某个查询应该显示怎样的回答。
哈桑:很快,大概就六到八周的时间,我们构建了谷歌的整个架构。大部分都是我跟谢尔盖俩人在凌晨2点到6点疯狂地工作。我们基本上都是通宵干活,主要是因为,如果我在白天写这些代码的话,我的老板肯定会臭骂我一顿,因为开发搜索引擎算不上什么研究……我们把搜索引擎搭得差不多后,拉里开发了一个小的交互界面。你前往这个网络页面,然后在页面的最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方框,跟现在的谷歌搜索框有点类似。就一个单独的方框,边上是另一个下拉框,显示“您希望使用哪个搜索引擎?”
布拉德·坦普顿(Brad Templeton,互联网先驱和专家):那会儿搜索引擎一抓一大把,有Excite、Lycos、AltaVista、Infoseek、和在加州伯克利校园内开发的Inktomi等。
哈桑: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搜索引擎,然后输入你要查询的内容,再点击搜索,接着,在左边,会显示你选择的搜索引擎返回的查询结果,右边则是我们的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这样你就可以比较两边的结果。所以,拉里还找了所有这些搜索引擎公司,试图向他们推销PageRank。
切瑞顿:他们开始走上了授权PageRank的特殊冒险,我觉得谷歌的一些有趣的早期故事可以从这时候追溯起——如果有人有意突袭谷歌的话,那时候他们只要以200万美元买下整个产品或者其他方式都可以。
哈桑:我记得有次跟Excite的首席执行官乔治·贝尔见面。贝尔选择了Excite,然后输入“互联网”,左边弹出来一列几乎都是搜索结果,右边谷歌搜索的那一列则显示的大多都是和N.S.C.A. Mosaic(早期停产的网页浏览器)有关的内容,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性较大的结果。乔治·贝尔多这样的结果显然很是失望,然后就非常有意思,他很戒备地说,“我们不需要你的搜索引擎,我们不想让别人这么轻易地搜索到他们想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希望人们可以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听来很荒唐,但当时还是有道理的:让人们停留在你的网站上,别让他们离开。我记得,后来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拉里和我讨论说:“用户去你的网站做什么?不就是搜索吗!然后你居然看不上这么棒的搜索引擎?简直没道理。那家公司肯定要完蛋,你说呢?”
布林:搜索被看做是另一种服务,一百种不同服务中的一个。通过这一百种服务,他们认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放大一百倍。
切瑞顿:我想大约是在一年后,他们又找到我说,他们没找到任何愿意接受授权的地方,当然我那会儿没说,“早就告诉过你”,但我内心其实还是有点洋洋得意的。
布林:接着就到了1998年夏天。那时候我们四处寻找资源,我们从各部门偷来电脑,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些电脑组装在一起,但这些电脑品牌都不同,各种的都有。
凯恩斯:他们把服务器从装货区卸下来,光是靠着口口相传,巨大的流量一再让服务器崩溃。
佩奇:我们导致整个斯坦福的校园网陷入瘫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可以登录斯坦福的任何一台计算机。
凯恩斯:最后,他们委婉地被请离校园。
佩奇:斯坦福说,“你们几个要是失败地话,再回来继续完成你们的博士学位吧。”
切瑞顿:他们认为自己在融资上有困难,我倒觉得钱不是大问题,所以我大概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吧,我就联系了安迪·贝克托斯海姆。
布林:安迪·贝克托斯海姆是太阳计算机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斯坦福的一个校友。
安迪·贝克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电气工程师,投资者和企业家):问题当然是,“你怎么赚钱?”于是,他们的想法是,“好吧,我们将拥有这些赞助的链接,当你点击链接时我们会收取5美分。”然后,我在脑海中快速进行了一个计算:好吧,如果他们每天能获得100万次点击的话,5美分一次那就是5万美元一天——这么算的话至少他们不会破产。
切瑞顿:安迪立马站起来,走向他的保时捷,差不多是用跑的,拿了支票簿,折回来,给他们写了张支票。
布林:他给了我们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十分地出人意料。但是支票的收款人却是“谷歌公司”,当时谷歌公司还不存在,这就很令人头疼了。
坦普顿:接着他们就去了“火人节”。
雷·西德尼(Ray Sidney,谷歌第五号员工):布林在网站上放了一个“火人节”的图标,这就是第一个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
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谷歌第二十号员工,前雅虎首席执行官):这更像是“不在办公室”的通知,上面写着,“我们都去参加火人节了”。
坦普顿:一支谷歌小分队驻扎在火人节。我还记得我对玛丽莎说了些十分粗俗的话,我说我想看到你赤身裸体的样子,我真不该说这些话的。她应该不记得了,希望是这样。
梅耶尔:要知道,那会我们都很年轻,除了朋友,我们也都是同事。
哈桑:我负责帐篷,谢尔盖负责食物。所以,他就去了陆海军补给店,买了所有的口粮——MRE口粮(美国陆军开发的一种个人野战口粮)。这些口粮不得不说很神奇。你在那个小袋子里放点水之后,大概里边是有什么化学物质,一会水就变得滚烫,里边的食物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你都不需要什么炉子,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开着谢尔盖的车去了火人节,然后在那里四处闲逛。
凯恩斯:他们递给我一个文件夹,里边都是10万美元、20万美元这样的支票,写支票给我们的人有安迪·贝克托斯海姆,杰夫·贝索斯,大卫·切瑞顿。他们连续好几周都坐在我的车后座,因为我实在忙得没时间,甚至连开银行账户的时间都没有。
西德尼:我之前还从未在一家早期的创业公司工作过。那种体验,非常紧张激烈。在谷歌的第一周,我就通宵了两晚。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疑问。所以我们希望尽最大能力让一切运作起来,所以我们拼了命地工作。我们心中有伟大的愿景。
凯恩斯: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商业计划,他们告诉我,使命就是“统治世界”。我想,好吧,不管了,只要确保能给我发工资就好了,几年后公司破产了我反正还能干自己的。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编辑,未来主义者和畅销书作家):当我遇见佩奇的时候,我说,“嗨,拉里。我还是不太明白。免费搜索能有什么未来?我不懂你们以后能做什么……”拉里回答我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其实不是搜索。我们正在创造A.I.(人工智能)。”所以,从一开始,谷歌的使命就是利用搜索成就人工智能,而不是利用人工智能让他们的搜索变得更好。
凯恩斯:统治世界?我们已经做到了。当年,七个人在某一人的房子里,睁开双眼就疯狂地工作,那时他们讨论的就是——统治世界。
第二部分:“好吧,现在我们有机会...”
西德尼:一开始,谷歌的办公室就在苏珊·沃杰克基(Susan Wojcicki,谷歌广告业务高级副总裁)家里,占用了房子一半的空间,还包括一个车库。
凯恩斯:我们可以使用苏珊放在车库里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我们是在卧室里工作的,而不是在车库。车库一说不过是坊间传闻罢了,大家似乎觉得每一家初创企业都应当在车库办公一样……“聚会”非常震撼——不管是谁来看都会觉得很震撼,更不用说以一个办公聚会的标准来衡量了。大约会有100个人来参加聚会,我们还会从电影公司找一些道具。我们还设置了一个热水浴池,你可以在那儿洗个热水澡。
切瑞顿:将办公室定在大学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坦普顿:正是这个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办公区域配备了巨型气球椅之类的东西,这也成为了办公室的装饰主题。
梅耶尔:熔岩灯比较特殊,因为它们采用了谷歌logo里具有的所有色彩元素。弹跳球是拿来装饰的,不过也很好玩。
查理·艾尔斯(Charlie Ayers,谷歌第一位主厨,因此也是早期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我还记得自己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拉里就在那些有把手的巨型球上蹦蹦跳跳,有点像是你还是孩子时会在玩具反斗城买的那种。这个态度确实非常不专业,也不太像是一个公司。过去,我时不时会和感恩而死乐队合作,所以我非常理解有人会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做事情。但在我看来,从一个外行人看来,这场面试很古怪。我从没经历过这种面试。离开的时候,我心里还想着这群人太疯狂了。他们不需要一个主厨。
凯恩斯:当我知道他们雇佣了之前曾为感恩而死乐队工作的主厨时,我非常惊讶。很明显,和感恩而死乐队相关的东西也会随着查理的到来被带入到谷歌。
艾尔斯:拉里的父亲就是乐队的死忠粉,他之前会负责每周日晚与感恩而死乐队相关的电台脱口秀节目。拉里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长大的。
佩奇:我们就是不怕麻烦,愿意招募一些与众不同的人。
埃尔斯:这里可没什么对于着装、长相、气味甚至是行为举止的要求。公司内不成文的口号就是:你穿着西装出现?那你是不会被雇佣的!我记得一些穿着西装来面试的人,他们说道——“回家换套衣服吧!做你自己!明天再来面试!”。
凯恩斯:我们觉得一周带宠物来上班一次没什么问题。这一规定之下,大家就开始养蜥蜴、猫猫狗狗了——我的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带着宠物来上班,那你是决计没法认真工作的。
道格拉斯·爱德华(Douglas Edwards,谷歌第59位员工):我们会去加州斯阔谷搞团建,所有人都必须要参加。这成为了公司特色。
西德尼:第一次滑雪旅行是在1999年上半年。这些年来,滑雪一直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
艾尔斯:在斯阔谷的滑雪旅行中,我会举办一些未经批准的派对,最后公司的态度就是——“好吧,我们就满足查理的要求吧。”然后我举办了查理的小窝派对。我会请现场乐队、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们买了一卡车的酒以及很多大麻。我记得有人走过来对我说,我产生幻觉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拉里和西德尼身边围着一群热辣的女孩,她们就像是他俩的行政后宫一样。我称这些女孩子是L&S Harem。数年之后,这些女孩都成为了谷歌公司不同部门的负责人(谷歌的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
凯恩斯:相比之下,你会对拉里的私生活比较放心。我们总是有点担心西德尼会和公司里的某个人约会......
艾尔斯:西德尼就是谷歌的花花公子。他曾被人当场抓包——他和公司内的同事一起去做按摩。
凯恩斯:我们没有制定什么规章制度。如果没有相关规定的话,你也无从阻止这件事。除了我是35岁之外,他们其他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荷尔蒙肯定会旺盛一些。
艾尔斯: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告诉我,西德尼对此事的反应是,“为什么不能呢?他们是我的员工”。但是你的员工不是用来做这个的,这不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
凯恩斯:我的天哪,很有可能会弄出性骚扰指控的事情。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艾尔斯:当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曾任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副总裁)加入公司的时候,我发现公司内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穿着西服来面试的人也会被录用。
凯恩斯:当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加入公司的时候,我心想,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了。这家伙很严肃,也很实在。他很高调,当然他肯定是一位工程师。不然,拉里和西德尼是不会雇佣他的。
第三部分:“我们确实在做的一些事情”
艾尔斯:公司里的很多人都很期待他的到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老家伙。在施密特来之前,你在办公楼里可能很少会看到一些成年人。
凯恩斯:在他刚上任那几天,他在公司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讲。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谁。”他说是 微软 。听罢,所有人都流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威诺格拉德:我还记得自己参加过的几次高层会议,那都是讨论在微软的监测下,谷歌可以做些什么。事实上,“加拿大”就是谷歌为微软起的代号,因为它在北方且国土面积很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微软觉得谷歌是威胁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镇压它,所以公司希望能确保不会触发这种情况。
埃文· 威廉姆斯 (Ev Williams,Blogger、 Twitter 和Medium的创始人):大家很担心Windows下一个版本会在操作系统上嵌入搜索功能。那我们要怎样与之竞争呢?
凯恩斯:所以,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大概是——啊!哇!他认为我们对微软来说是一个威胁。你在搞笑吗?可他的那段话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影响力也许比我想得要大得多。
梅耶尔:这比我们之前实际讨论过的愿景要大得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爱德华:如果你看过拉里和谢尔盖(Sergey Brin,谷歌联合创始人)在斯坦福写的论文,他们当时在文章中谈到要开发一个搜索引擎,并明确指出广告是一种错误且不当的形式。如果你开始出售广告位,搜索引擎就会变味儿。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在谷歌上做广告的想法。
西德尼:之后,大家读到了搜索广告给其他公司带来了多少盈利的文章,这一决定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把钱拱手让人一样。
爱德华:当时创收的压力也非常大,因此拉里和谢尔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广告并不一定都是邪恶的——如果它真的有用的或相关的话。
保罗·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Gmail创始人):2000年年初,一场会议决定了公司的价值观。他们邀请了一批曾在谷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 我坐在那里,试图想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往常那种“追求卓越”的陈词滥调。我想要想出一些东西:一旦你把它放进去,就很难拿出来了。
坦普顿:“不作恶”便是那时候提出来的。
布赫海特:这是我突然想到的。
布林:我们想要给“善意的力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永远做正确、合乎道德的事情。最终,“不作恶”似乎是最简单的总结。
布赫海特:这对其他公司来说也是一种警醒,尤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我们看来,当时这些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剥削用户。它们通过出售搜索结果来欺骗用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因为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搜索结果是广告。
布林: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滑坡谬误。
坦普顿:当时,谷歌已经成为一家非常大规模的公司了。
凯恩斯:我们搬到了美国硅图公司之前所在的园区,还有一些它们的员工在那里工作,他们见到我们并不高兴。
梅耶尔:当时S.G.I.的运营状况并不是太好,整个园区里大约有50人。
吉姆·克拉克(Jim Clark,S.G.I、网景的创始人):它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凯恩斯:我们当时的感受类似于,“耶! 这是我们的台球桌和我们的糖果! 耶! 我们是谷歌!”他们看着我们在窗外打排球,像是在说:“Fuck you!”
克拉克:他们因为自己错过成为网景的一部分而感到苦恼。
梅耶尔:我们当时也有点不尊重人——在大吵大闹。
凯恩斯:我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我们只是太蠢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失去工作。他们则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只是看着新人的到来——开心、迫不及待,打着球。
比兹·斯通(Biz Stone,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谷歌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就像是奇怪的孩子玩耍的地方。成年人在那里工作,但是那里都是一些巨大的、五颜六色的弹力球。埃里克·施密特有一个蜿蜒曲折的滑梯,他可以通过它离开办公室——现在看起来太不正常了。
凯恩斯:我效仿斯坦福大学制作了员工手册并且确立了企业文化——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来自那里。
肖恩·帕克(Sean Parker,Napster的创始人、 Facebook 的第一任总裁):谷歌确实在尽可能将他们的工作环境打造得和研究生院一样来吸引出色的工程师。谷歌可能会说:“哦,别担心,这会和你读研究生一样。这不像是出卖劳动力或者进入企业打工,你仍然是一个学者,你现在只是在谷歌工作而已。”他们凭此吸引到了很多非常聪明的人。
斯通:谷歌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这里会发生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我会像参观威利·旺卡巧克力工厂的小孩一样,到处走走查看事情是否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佩奇:乐高思维风暴(LEGO Mindstorms)。员工就是小小的乐高组件,里面有一台计算机,他们就像带有传感器的机器人。
凯恩斯:我记得他们制作了一个橡胶轮子,让它在纸上滚动。我就说“你在干嘛?”。他们回我说,“唔,我们想扫描每一本书和出版物,并把它们放到互联网上。”然后我说,“你们疯了吗?”他们说,“唯一阻碍我们的就是翻页的问题。”
斯通:有一天,我走进一个房间,却发现有一大群人因为一些配备了灯光、脚踏板和书的自动装置感到茫然。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扫描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然后我说,“好吧,那你们继续。”我清楚地记得我径直走向一个我以为是储藏室的地方,地上有个印度人没穿鞋。他拿着一把螺丝刀,把所有的录像机都拆了,看起来像是整晚没睡或者怎么的。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正在录制所有的广播电视。”然后我说,“好吧,你继续。”
梅耶尔:我们进行第一次街景实验的那天,我也在现场。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只是想发泄一下。我们从沃尔夫相机公司租了一台价值8000美元的相机,按天租的话其实价格要低很多。我们开着一辆蓝色的大众甲壳虫车,并在座位上放了一个三脚架,上面放着相机。我们开始在帕洛阿尔托行驶,每隔15秒拍一张照片。然后,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用照片拼接软件试着将这些图片拼接在一起。
凯恩斯:拉里和谢尔盖是最重要的投资者。那是他们的真爱。
梅耶尔:我会主持每周一次的头脑风暴会议,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大的想法。有一周,我用太空缆绳为引子开始了会议。我们开始进行头脑风暴,有人想用碳纳米管来建造它,然后想着可以用它来给月球送披萨吗?
爱德华:谢尔盖则会抛出一些营销创意。他希望能将我们公司的logo投射到月球上。他想把整个营销预算都用来帮助车臣难民。他想制造出谷歌牌的避孕套并分发到高中。在谷歌,大家提出了许多想法,其中大部分从未成为真正的项目。但是如果拉里和谢尔盖提出了一些点子,你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会做做表面功夫、假装在意一下的。
梅耶尔:有些想法,我们真的有去实现它们,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在头脑风暴会议中就曾提过这一点。
斯通:这很奇怪,真的很奇怪,但是也很棒。
艾尔斯:公司的整个氛围就是专注于发展、发展以及发展。
凯恩斯:到了2003年,谷歌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大概有2000员工,人们都在谈论上市的问题。
凯恩斯:上市。赚钱。上市。上市。这在很多人心中都是最重要的和优先考虑的事情。
艾尔斯: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很多之前一直待在谷歌的人都希望能出去喘口气。他们在等待,甚至不再工作。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
西德尼:我感到筋疲力尽了。我感觉不到任何动力。你知道那种感受吗?我想的就是,我应该要离开这里。
艾尔斯:很多早期员工都在观望,大家都想知道谷歌上市之后能值多少钱。有很多分心的事情要考虑。
西德尼:起初我以为,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两个月,我就能重新憋起一股劲。但这事情一直没能发生。我在2003年3月离开了谷歌。
艾尔斯:随着IPO的日程更加接近,大家的心思越飞越远。他们对钱看得太重。
约翰·巴特利(John Battelle,《Wired》杂志的创始编辑、企业家兼作家):事后看来,谷歌2004年的IPO和1995年网景的IPO一样重要。90年代后期,所有人都对互联网的存在感到兴奋,但事实上,世界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使用互联网。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谷歌上市,重新将互联网打造成了一种媒介。
爱德华:在IPO之后,它变得愈加沉默寡言,开始有意识地去追求更多指标数据——这可能有利于公司发展。但这种企业文化与过去谷歌给我的感受是不同的,我还是喜欢之前那种企业文化。
艾尔斯:他们说,“我们现在是上市公司了。”虽然员工士气高涨,但是2004年并不是谷歌发展最好的一年。他们开始让更多的人去上戴尔·卡内基的课程。
凯恩斯:拉里和谢尔盖过去常常用手握着刀叉,舀着东西吃。他们常常在距离盘子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把食物舀进嘴里。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样。现在,他们必须学会不要那样做了。
艾尔斯: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去参加公共演讲班、媒体培训班以及领导力课程。
凯恩斯:再也没有人会有一些超级不好和让人感到恶心的行为了。但这真的很令人沮丧。经过训练,这种人性的本真似乎已经在他们身上渐行渐远——所有人都是如此。(木尔 芒立)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