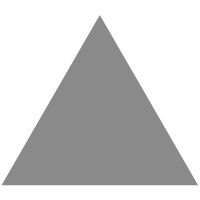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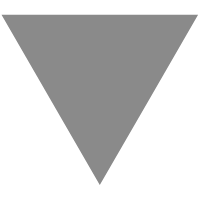
他有焦虑症,我只有焦虑,但是我们都有药吃
source link: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333151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他有焦虑症,我只有焦虑,但是我们都有药吃
他有焦虑症,我只有焦虑,但是我们都有药吃
去年8月,男票被安排了新的工作职能:除了日常医务和科研工作,还要负责科室行政事务。上级这样安排的原因很明确,对于处在职业上升期的年轻医生来说,承担一定管理职能是必要的。
朋友们听说以后,都对他露出了“咦”的表情。倒不是说这份职责有多难,只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人缺乏管理技能还害羞,一下子让他协调几十个人的开会、值班、加班、请假,还要和医院行政部门打交道,这根本是噩梦具象化嘛。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科室那阵子特别难。老医生退休,新医生没到岗,两项保障任务必须24小时有人待命。男票硬着头皮干了一阵子,发现实在协调不过来——排班一周改8次,吃个午饭接了7个电话要换班,已经排好的医生被调走去开会、上课……日常都是这样的:刚安抚完候诊室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开始大喊大叫的焦躁病人,正狂奔去急诊的路上,各路领导又打电话过来咆哮“你怎么不看群?!”。
我有几次看到他站在厨房水槽前面,手在抖,试着深呼吸。
症状初现,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
那段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过工作压力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来自各方面的职业压力通常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无视其中一些,拖延一些,或者反抗一些。
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选择会少得多——你知道如果你不出现,也许有人会死。
性格温柔、无法拒绝别人,也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他私下里对我说:“我觉得如果不能安排好科室的行政工作,都是我的错,是我能力不够……”
我说:“首先你要意识到,既然要给别人安排工作,你就没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男票嘤嘤嘤在沙发上缩成一团:“我就是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嘛!”
 性格温柔、无法拒绝别人,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丨Pixabay
性格温柔、无法拒绝别人,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丨Pixabay某天我刚下班,他同事发消息给我说他状况不对,现在在挂急诊,但同事那里还有很多病人没法陪着,让我快点过去接一下。
我在高峰车流里堵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医院,男票独自蜷缩在更衣室角落一张小躺椅上打着颤。问了一圈,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姐姐说可能是惊恐发作引发了通气过度。
这时他同事终于看完了当天的病人,过来跟我说:“他怎么会惊恐发作呢?看着挺开心健壮的小伙子呀,是不是心事太重啦?让他多放宽心呀……”
我:“其实我觉得心事重是焦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人谁还没点儿创伤呢,回头去精神科看看,该吃药吃药呗。”
同事一副“现在小年轻怎么把去精神科说得那么容易”的表情。
之后男票在家也发作过一两次,独自缩成一团发抖,显然已经到了应该进行干预的时候。既然职业压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就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作为医生和医生的伴侣,我俩对精神问题的治疗一点不怵,精神病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科学,经费可多了!
我没有陪他进诊室
我俩摸索了半天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挂号系统,发现周末都约满了,而男票的工作量又不允许他工作日请假。暂时约到三周以后,但才过了一两天,我忽然收到男票的消息:“我不行了,你能不能来接我下午去医院。”
我冲进科室的时候男票正和上级开会。男票看到我,小心翼翼地对上级说自己下午无法工作得去看病。
上级声音一下子焦躁起来:“你突然要走我们这边怎么办?”
他低头咕哝着,好像挨老师骂的大块头。
好在老板数落两句还是放人了,我握着他的手问:“被老板骂难不难过?”
他说:“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了。”
到了医院一看,门诊自然是没有的,好在挂到了当天的特需号。候诊室里,他咬着牙紧握双手,我感到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着,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
男票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丨图虫创意
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的默契、多年的深厚情谊、以及我能够为他挺身而出的所有决心,都不能替他对抗此时的痛苦。疾病是人自己的命运,我可以陪着他,但他自己才是那个选定的勇者。
因为这个突然的认知,我没有陪他进诊室。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当那个在患者旁边替他阐述病情的人。我不想假装自己能成为拯救者:勇者走出正面对抗魔王的那一步,一定是他自己的决定。
没一会儿他出来了,神色轻松了不少。
“中度焦虑,”他说,“医生还说:都是医生,他懂的!”
配完药,我问:“你要不要休几天病假?”
男票突然又紧张起来:“不知道,我决定不了……”
“你都这样了好好休息吧!”我拉着他冲回医生诊室,“医生他能开病假吗?”
“你这情况可以开啊,”医生刷刷写病假单,“给你先休俩礼拜,最多了,两周后没起色再来开!别怕,会好的!”
看完病我俩为了庆祝成功就诊,决定绕路去吃蟹粉面。
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医疗状况
当时我没感到有多难。一方面,确诊意味着治疗;另一方面,我们俩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人生在世哪有不生病的,有得治不是很好吗?
不过,确诊之后我的第一反应也许和很多患者家属一样:“我的伴侣得了焦虑症,是我让他感到不幸福了吗?”
我知道这个念头没什么建设性,它只是患者家属的自然忧虑,但我也没有隐瞒这种感受。亲近人的小心翼翼是瞒不过去的,而我知道他会因为我的自责而自责。我不希望他有“我让家人受累了”的感受,这只会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所以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感觉,并且问他:“现在,你是医生,我是患者家属,你觉得我怎么做才是对伴侣的真正支持?”
他说:“你只要在我求助的时候陪伴,别的和平时一样就行,不需要额外做什么。”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医疗状况。我的伴侣病了,和疾病谈感情或是讲道理没什么用,询问“你怎么会得这种病”也没什么意义。
他需要的只是治疗,以及情况偶尔失控时周围人的合理宽容。我自然会学着接受他的处境,至于工作嘛——医生同事们,都懂的。
这件事对我们心情的影响也就这样了。偶尔同事逗他,男票还会噔一下跳到别人背后挠乱别人头发,然后被同事绕办公室追着打。
同事:“这是药物副作用吗?”
我:“不,这是天然逗比。”
药物副作用:不太可怕甚至有点好笑
当时还有件值得一记的小事。服药的当晚,男票盯着三种药皱眉头。我也很紧张:“听说精神类药物会有奇怪的副作用,会是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种(也是唯一一次)副作用:男票躺在床上,背部不停抽搐。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痉挛,但他突然坐起来去厕所,接着去厨房拆了包饼干吃。然后他开始循环“厕所-床-饼干”,期间不停扭着手试图摸到自己背部,躺下的时候就不住挥舞手脚,好像狗子做梦追兔子。
我试图和他说话,但他意识似乎并不清楚,一直昏昏沉沉地舞动手脚,看起来十分诡异。
已经是半夜了,于是我给远在德国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发消息,向她描述了男友此刻的状况。她让我再观察一下。
我观察了一会:“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死。”
既然不会死我就不打120了,我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盯着他。这时循环绕圈的男票已经被我捉回来躺平两三回了,但他仍不受控制地乱动,而且意识模糊之下他大约知道自己不能入睡,忽然爬起来要去拆安眠药。
“要命了你还想吃第四种精神类药物!”我飞扑过去一把摁住他。
好在这人此刻像僵尸一样傻,被摁住就忘记自己要干啥了。他像猫一样软绵绵地做出各种角度诡异的扭动,气氛一度十分尴尬。最后我说:“要不你去吐一下吧?”
小僵尸点头,乖乖走进厕所吐了两回,终于安安稳稳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听我形容以后兴致盎然地跟精神科同事讨论,猜测可能是一种较罕见的副作用叫“锥体外系反应”。
我们次日就去咨询了这个谜一样的副作用,医生去掉了一种药,之后就再没什么好玩的反应了。后来我才知道药物会有适应过程,最开始的副作用不一定会一直持续。
几周以后,德国朋友又来追踪剧情进展。
我:“不知道,好像现在只吃一种药就行了,不谈工作什么症状都没有。”
朋友:“断药的指征是无业,真有道理。”
我:“可不是,我就说精神疾病是现代文明黑暗面的隐喻。”
男票的治疗进程十分平稳,一段时间以后他鼓起勇气,辞掉了行政职务(什么也没有发生)。随着治疗进展,他不仅能更好地应付工作压力,而且有动力和能力去承担更多责任、尝试更多可能性。一年过去,他现在转而承担科室的各种技术支持和学术工作,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看起来十分轻松,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正如我们之前想的那样,工作压力只是给原本就艰难平衡的感觉加上了最后一根羽毛,而积极治疗夯实了脚下的道路,让他不再为羽毛的重量忧心忡忡。
此前,我的工作包括新媒体运营,年初疫情期间,每天打开社交网络都要经历海啸般的情绪冲击。到了四月,我感到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经常一个人呆坐着,记忆有些模糊;明知有事要干却打不起精神来,想到没有完成的任务会背后发毛、脖子酸痛、手心发胀。原本心爱的健身环也不香了,偶尔还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原本觉得随着疫情缓解就能过去,但状况并没有改善,呆坐着无法行动的情况从一两周发生一次增加到了一周两三次。6月底的一个早晨打开微博,我忽然浑身冷汗、干呕,接下去两个小时里几乎无法思考,也无法站起来去做别的事。
我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第一时间预约了次日早晨的精神科门诊,跟医生说了两句话就被赶去做量表。
监督我填表的医生看到我勾了“工作量显著增加”说:“你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我:“多次取样以后做分布只要增加10%就肯定显著了!”
“显著不是这个意思!”医生翻了个白眼把勾取消了。
拿着量表回门诊,门诊医生翻翻结果:“你没病。”
我:“怎么没病!我焦虑感已经出现四五个月了,一看社交网络就惊恐,意念消极无法摆脱而且持续时间从半天增加到连续四五天……”
医生:“正常的,给你开个睡觉的药回去好好睡。”
总之我拿着药滚了。出了医院收到男票消息:“怎样,你是哪种精神病?”
我:“医生说我只是没睡好,让我好好睡觉。可我明明每天睡八个小时!”
男票陷入沉思,过了会说:“好消息是你没病,坏消息是你没治。”
我:“我都这么难受了还没病吗!”
说完我突然意识到,虽然自己确实感到痛苦,但对生活、时间的控制还行,远远没有表现出男票去年的那种外在状态。但是这种程度已经令我难以忍受。
所以作为疾病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和一般人轻微、偶发的“心情不好”、“好丧”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后者有时也意味着真实、剧烈的痛苦——甚至也可以得到医疗支持。
睡得好了,我感觉焕然一新
带着紧张和好奇,乖乖遵医嘱服药。男票担心我出现什么奇怪的副作用,在边上守到十一点,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觉焕然一新。长期以来,我习惯于凌晨两三点开始做噩梦,然后六点多醒来灌上400毫升咖啡开始工作,从没感觉哪里不对。但前所未有地一夜无梦后,我醒来感觉整个世界的颜色都变了,变得更鲜明。效率和反应速度也有了明显提高,一个典型表现是我飞快学会了游戏里从没撸顺过的近战操作。
我被惊呆了:“这什么药物,效果也太好了吧?我甚至觉得自己比以前聪明了10%!”
男票:“你吃药都快24小时了早代谢完了,你就是睡够了。”
接下来几个月,我过上了“我好喜欢睡觉+我好喜欢起床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地积极,效率骤增,曾经萦绕不去的各种忧虑都不可怕了。至于药物反应,热爱工作算吗?
和朋友们分享以后有人问:“什么药效果这么好?我从上班打完卡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想玩手机……”
我:“请不要对精神类药物有这种妄想,我只是没睡好,但我喜欢工作的,原本就不想上班大概没得治。”
朋友:“好的,那我不努力了。”
逻辑通顺无法反驳。
中间也有些小波折,几个月后我换了种药,吃完倒头暴睡了两天半。
尽管药效太神奇,男票还是念叨着药代动力学之类的,要我继续按医嘱服药。好在第三天开始嗜睡的状况有所缓解,到了第六天基本能在正常时间醒来,不会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一周以后我冲去医院复诊:“医生!新药不行!吃了根本醒不过来!我这周啥事没干光睡觉了!”
医生一拍桌子:“好哇!说明你对这药反应好!睡不醒怎么办?我告诉你,减量,吃半片,再不醒,吃1/4片,过一阵子你就能停药了。”
我:“竟有这等好事?”
结果就像医生说的那样,这等好事真的在发生,如今药量也在遵医嘱递减。随着每月拜访一次宛平南路600号,我情绪积极、活力满满,念着“不要怂就是干”,把过去一直拖延的好几个任务都往前推了一大步。
我有许多朋友确诊抑郁症或焦虑症,活到这么大,周围人当中因抑郁去世的也有三四个了。这些经历让我对治疗的态度非常积极:因为伴侣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对疾病都没有太多污名观念和偏见,只有发现、面对、干预。
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常跟我科普各种医学知识,更是因为我不再感到疾病可怕。面对疾病,我们有许多可以做的事,甚至长期睡不好这样的事也有切实有效的诊疗手段。
经过这一年多的先后就诊,我们互相确认了一件事:即使是听起来很难缠的精神问题,我们是能够自己面对、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支持、能够彼此接纳的。它有点难,但也没有那么难。爱是力量,这不是言情小说里浮夸的戏剧表演,而是鸡零狗碎的真实生活中,你真正拥有的东西。
偶尔我仍然会有低潮。我会对男票说:“对不起我真是个糟糕的伴侣。我为那些琐事感到如此痛苦,让你也紧张不安、不知所措,我为自己这样感到抱歉。”
男票:“你说什么呢,我们俩当中我才是有病的那个!”
崔飞环 | 北京安贞医院精神心理科医师
约20%的成人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惊恐发作(panic attack),然而符合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PD)诊断的只有2%。
惊恐发作是一种严重的焦虑发作,发作时有明显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如心悸、胸闷、胸痛,严重者伴有濒死感,不发作的时候也会担心再次发作。惊恐发作是一组症状群,可出现在任何焦虑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中,如抑郁症、PTSD等。惊恐发作可以随时随地出现,不分场合。而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惊恐障碍主要是指反复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
凡人皆需侍奉。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生也是如此。文中的患者似乎扮演了更多照护别人的角色,责任感驱使下使自己的行为满足医疗系统、社会规范对好医生、好同事、好科研工作者的要求;但自己要休息、睡眠这种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却被压抑了。很多时候冲突和被压抑的需求不能被意识到,两部分发生冲突时自我协调不良,难以找到真正的冲突对象,便产生了焦虑。
心理障碍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因素、后天依恋关系、家庭环境以及心理应激等方面,作为患者家属很难单一归因。家属能够接纳患病这一事实、共同面对疾病,对患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在焦虑症的治疗方面,可以使用药物和(或)心理治疗,而药物以抗抑郁剂为主,副反应常在药物治疗初期出现,随着治疗进程药物副反应会减轻。如果实在不能耐受药物,治疗过程中医生也会做换药处理。
然而并不是感到痛苦就一定是心理障碍,正常的焦虑与疾病性的焦虑不同,通常与客观威胁成比例,不涉及压抑或其他内心冲突的机制,也不需要启动防御机制,并在意识层面觉察、建设性地改变。如文中的患者家属,在疫情期间接受大量信息冲击后出现应激反应,心身不适,但并没有社会功能的损害,治疗上也可以以心理教育、放松、调整生活节律为主。
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疾病、死亡时具有其脆弱性,有意识的焦虑虽然痛苦,但是可以自我整合、进步。生命的目标不是没有焦虑,而是在焦虑的情况下继续前行。
个人经历分享不构成诊疗建议,不能取代医生对特定患者的个体化判断,如有就诊需要请前往正规医院。
作者:哒哒子和锤锤美
编辑:黎小球

本文来自果壳病人(ID:health_guokr),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有需要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